“羽墨美甲”锚定“一站式”新赛道,明星品牌破解美业服务断层难题
“羽墨美甲”锚定“一站式”新赛道,明星品牌破解美业服务断层难题
“羽墨美甲”锚定“一站式”新赛道,明星品牌破解美业服务断层难题将(jiāng)SpaceX收归国有?
最近,美国爆发了一场颇具戏剧性(xìjùxìng)的争执:世界首富马斯克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陷入了激烈冲突。这场看似“摔跤秀”式的争吵虽然有些荒诞,但其中包含的权力威胁和政策风险却(què)真实而严肃(yánsù)。
马斯克的企业不仅仅是(shì)商业公司,更承载着美国国家运作的关键(guānjiàn)部分,众所周知,尤其是他旗下的SpaceX和Starlink。SpaceX是一家私人太空(tàikōng)公司,为美国政府和其他客户发射卫星、运输(yùnshū)宇航员(yǔhángyuán)。2023年末,它负责了全球90% 的太空发射重量,基本垄断了发射服务。载人(zàirén)飞船“龙”号(Dragon)是目前唯一能将美国宇航员送往国际空间站的交通工具(jiāotōnggōngjù)。美国政府多个部门,包括(bāokuò)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都依赖SpaceX的服务。
 当地时间(shíjiān)2025年6月7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SpaceX公司(gōngsī)猎鹰9号火箭于凌晨0时54分发射升空。
Starlink是(shì)SpaceX的全球卫星互联网服务,目前占据全球约三分之二的卫星总量(zǒngliàng)。用户只需一根小型接收天线,就(jiù)可以(kěyǐ)在世界任何地方接入高速网络。在俄乌(wū)战争中,马斯克可以决定是否允许乌军使用Starlink来作战——这给了他类似主权国家的权力。
最近,特朗普威胁要切断马斯克的政府合同资金(特别是SpaceX),作为政治报复。而马斯克也不甘示弱,暗示(ànshì)如果(rúguǒ)遭到(zāodào)打击,他(tā)可能会停止某些关键服务,比如“关闭龙飞船”或干扰美国军事通信。
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是特朗普的(de)前首席战略顾问,现在(xiànzài)又(yòu)回到其身边。他提出一个大胆建议:政府应该动用《国防生产法》,将SpaceX收归国有。《国防生产法》(Defense Production Act)是一部(yībù)1950年在朝鲜战争背景下(xià)颁布的联邦法律,允许(yǔnxǔ)美国总统在国家(guójiā)紧急情况下优先调配工业资源,以支持国防与国家安全目标。这部法律在新冠疫情期间也曾被(bèi)特朗普用来强制企业生产呼吸机和个人防护装备。班农的意思是:SpaceX已经成为类似“电网”或“军队通信”的基础设施,不能只(zhǐ)由一个人控制。“基础设施”在这里不仅仅指(zhǐ)物理层面,也包括信息和战略意义上的“平台控制力”,即一个企业对社会运行的关键路径拥有(yōngyǒu)决定权。
虽然SpaceX的技术确实有优势(火箭可重复使用、发射(fāshè)成本低),但它(tā)也被业界指责为通过不公平竞争打压对手(duìshǒu)。以下是《纽约时报》曾报道的几起例子:
新一代的太空创业者们(men)试图(shìtú)模仿(mófǎng)马斯克,但他们对马斯克被认为采用的反竞争手段(指通过不公平的方式限制竞争对手,保护自己市场地位的行为)感到担忧。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公开挑战他。
蒂姆(dìmǔ)·埃利斯(Tim Ellis)受到了马斯克想造出能载人去火星的(de)火箭的激励,创办了Relativity Space(一个火箭制造公司)。后来他(tā)听说,有些与SpaceX有关联的人在试图阻止他为自己的火星项目筹钱(chóuqián)。
吉姆·坎特雷尔(léiěr)(Jim Cantrell)是2002年(nián)和马斯克一起创办SpaceX的(de)。后来他创立了自己的火箭发射公司Phantom Space。可是,两位潜在(qiánzài)客户告诉他的销售(xiāoshòu)团队,因为SpaceX在合同中加入了限制条款(合同条款中写明不允许客户同时使用竞争对手的服务),他们无法和他签约。
彼得·贝克(Peter Beck)是新西兰的(de)航天工程师,2019年曾和马斯克见面,谈他的公司Rocket Lab。几个月后,SpaceX开始以优惠价运送小型货物(小型货物指(zhǐ)体积或重量较小的货物),贝克和其他(qítā)业内人士认为这是(zhèshì)为了压制竞争对手、降低他们的成功机会(jīhuì)。
这些(zhèxiē)行为(xíngwéi)包括:低于成本发射,以极低价格让对手无法生存(shēngcún);“优先拒绝权(quán)”条款:客户若找到更便宜的(de)竞争者,SpaceX有权“抢单”;偏袒自己公司(如Starlink):同样是发射卫星,Starlink获得更便宜报价;干扰竞争对手融资;进入门槛高(需要巨额资本与许可)。这些都是典型的垄断行为。
之前学者Siva Vaidhyanathan在《The Nation》杂志(zázhì)上的(de)评论文章就认为,马斯克之所以成为21世纪最具(zuìjù)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制造了电动汽车或(huò)发射了火箭,而是因为他掌握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的力量形式——对全球互联网(hùliánwǎng)连接的控制权,特别是通过卫星互联网。他能够随意地打开(dǎkāi)或关闭数百万人的网络接入,就像扳动水龙头一样。
虽然SpaceX是私人公司,但它从公共资金中获得了大量支持(zhīchí)。Starlink的意义,在(zài)(zài)俄乌冲突爆发后变得极为突出(tūchū)。自2022年2月战争爆发以来,Starlink为乌克兰的平民和军队提供了关键的通信服务。马斯克最初同意在乌克兰上空部署大量Starlink卫星,费用由(yóu)他承担(chéngdān),而接收终端设备则由北约国家和私人捐助者提供。
但问题随即出现。马斯克(mǎsīkè)拒绝将Starlink信号延伸至被俄罗斯(éluósī)占领的乌克兰地区(dìqū)(例如克里米亚(kèlǐmǐyà)和顿巴斯),理由是他不想“卷入战争升级或制造重大军事冲突”。这种做法实际上默认了俄罗斯对这些地区的非法主张,完全无视乌克兰的主权、国际法和人权问题。
这就是一个危险的(de)信号:战争冲突中(zhōng)最基本的通信手段,竟然落入了一个私人(sīrén)企业家的手中。他不是依据国际准则或多边协议行事,而是凭借个人意志和判断,左右一个主权国家的信息生命线。
当地时间(shíjiān)2025年6月7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SpaceX公司(gōngsī)猎鹰9号火箭于凌晨0时54分发射升空。
Starlink是(shì)SpaceX的全球卫星互联网服务,目前占据全球约三分之二的卫星总量(zǒngliàng)。用户只需一根小型接收天线,就(jiù)可以(kěyǐ)在世界任何地方接入高速网络。在俄乌(wū)战争中,马斯克可以决定是否允许乌军使用Starlink来作战——这给了他类似主权国家的权力。
最近,特朗普威胁要切断马斯克的政府合同资金(特别是SpaceX),作为政治报复。而马斯克也不甘示弱,暗示(ànshì)如果(rúguǒ)遭到(zāodào)打击,他(tā)可能会停止某些关键服务,比如“关闭龙飞船”或干扰美国军事通信。
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是特朗普的(de)前首席战略顾问,现在(xiànzài)又(yòu)回到其身边。他提出一个大胆建议:政府应该动用《国防生产法》,将SpaceX收归国有。《国防生产法》(Defense Production Act)是一部(yībù)1950年在朝鲜战争背景下(xià)颁布的联邦法律,允许(yǔnxǔ)美国总统在国家(guójiā)紧急情况下优先调配工业资源,以支持国防与国家安全目标。这部法律在新冠疫情期间也曾被(bèi)特朗普用来强制企业生产呼吸机和个人防护装备。班农的意思是:SpaceX已经成为类似“电网”或“军队通信”的基础设施,不能只(zhǐ)由一个人控制。“基础设施”在这里不仅仅指(zhǐ)物理层面,也包括信息和战略意义上的“平台控制力”,即一个企业对社会运行的关键路径拥有(yōngyǒu)决定权。
虽然SpaceX的技术确实有优势(火箭可重复使用、发射(fāshè)成本低),但它(tā)也被业界指责为通过不公平竞争打压对手(duìshǒu)。以下是《纽约时报》曾报道的几起例子:
新一代的太空创业者们(men)试图(shìtú)模仿(mófǎng)马斯克,但他们对马斯克被认为采用的反竞争手段(指通过不公平的方式限制竞争对手,保护自己市场地位的行为)感到担忧。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公开挑战他。
蒂姆(dìmǔ)·埃利斯(Tim Ellis)受到了马斯克想造出能载人去火星的(de)火箭的激励,创办了Relativity Space(一个火箭制造公司)。后来他(tā)听说,有些与SpaceX有关联的人在试图阻止他为自己的火星项目筹钱(chóuqián)。
吉姆·坎特雷尔(léiěr)(Jim Cantrell)是2002年(nián)和马斯克一起创办SpaceX的(de)。后来他创立了自己的火箭发射公司Phantom Space。可是,两位潜在(qiánzài)客户告诉他的销售(xiāoshòu)团队,因为SpaceX在合同中加入了限制条款(合同条款中写明不允许客户同时使用竞争对手的服务),他们无法和他签约。
彼得·贝克(Peter Beck)是新西兰的(de)航天工程师,2019年曾和马斯克见面,谈他的公司Rocket Lab。几个月后,SpaceX开始以优惠价运送小型货物(小型货物指(zhǐ)体积或重量较小的货物),贝克和其他(qítā)业内人士认为这是(zhèshì)为了压制竞争对手、降低他们的成功机会(jīhuì)。
这些(zhèxiē)行为(xíngwéi)包括:低于成本发射,以极低价格让对手无法生存(shēngcún);“优先拒绝权(quán)”条款:客户若找到更便宜的(de)竞争者,SpaceX有权“抢单”;偏袒自己公司(如Starlink):同样是发射卫星,Starlink获得更便宜报价;干扰竞争对手融资;进入门槛高(需要巨额资本与许可)。这些都是典型的垄断行为。
之前学者Siva Vaidhyanathan在《The Nation》杂志(zázhì)上的(de)评论文章就认为,马斯克之所以成为21世纪最具(zuìjù)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制造了电动汽车或(huò)发射了火箭,而是因为他掌握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的力量形式——对全球互联网(hùliánwǎng)连接的控制权,特别是通过卫星互联网。他能够随意地打开(dǎkāi)或关闭数百万人的网络接入,就像扳动水龙头一样。
虽然SpaceX是私人公司,但它从公共资金中获得了大量支持(zhīchí)。Starlink的意义,在(zài)(zài)俄乌冲突爆发后变得极为突出(tūchū)。自2022年2月战争爆发以来,Starlink为乌克兰的平民和军队提供了关键的通信服务。马斯克最初同意在乌克兰上空部署大量Starlink卫星,费用由(yóu)他承担(chéngdān),而接收终端设备则由北约国家和私人捐助者提供。
但问题随即出现。马斯克(mǎsīkè)拒绝将Starlink信号延伸至被俄罗斯(éluósī)占领的乌克兰地区(dìqū)(例如克里米亚(kèlǐmǐyà)和顿巴斯),理由是他不想“卷入战争升级或制造重大军事冲突”。这种做法实际上默认了俄罗斯对这些地区的非法主张,完全无视乌克兰的主权、国际法和人权问题。
这就是一个危险的(de)信号:战争冲突中(zhōng)最基本的通信手段,竟然落入了一个私人(sīrén)企业家的手中。他不是依据国际准则或多边协议行事,而是凭借个人意志和判断,左右一个主权国家的信息生命线。
 当地时间2025年(nián)2月(yuè)11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特斯拉和SpaceX首席执行官伊隆·马斯克在白宫椭圆形(tuǒyuánxíng)办公室,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活动。
马斯克拥有的(de),不(bù)仅是商业成功,更是一种足以改变战争(zhànzhēng)进程的、从未有人掌握过的通讯(tōngxùn)控制权。过去的媒体大亨,如(rú)赫斯特(20世纪初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报业大亨,拥有多家报纸和媒体,他通过夸大和煽动新闻,特别是在美西战争期间,制造公众对西班牙的敌意,推动美国政府对西班牙宣战(xuānzhàn),他被认为是Yellow journalism的代表人物,利用媒体操纵舆论,激发民族主义和战争情绪,从而影响国家政策和战争走向),可以操纵舆论推动战争;金融巨头如J.P.摩根,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zhōng)资助参战国。但他们并(bìng)不具备像马斯克这样,直接通过技术(jìshù)平台“关闭战场Wi-Fi”的能力。
Starlink的“地理围栏(wéilán)限制”(geofence)丑闻反映了一个(yígè)严峻现实:马斯克可以凭一己喜好,决定一个国家的军队是否还(hái)(hái)能指挥作战,一个企业是否还能运作,一个媒体是否还能报道。他的情绪和立场,可能成为左右国家命运的变量。
乌克兰并(bìng)不是唯一被Starlink影响的(de)地区。事实上,马斯克正低调地推动一个更宏大的图景(tújǐng)——重塑全球数字通信系统,使之以他个人意志为核心。如今世界各国试图摆脱Meta(Facebook母公司(mǔgōngsī))、Alphabet(谷歌母公司)等美国巨头的控制,以实现“数字主权”。但在(zài)这一过程中,它们(tāmen)却在网络基础设施层面被Starlink套牢。
对于许多基础薄弱、地广人稀的(de)发展中国家而言,Starlink提供(tígōng)的高速网络是(shì)唯一(wéiyī)可行的选择。Starlink凭借“先发优势(yōushì)”,自2019年起就开始大规模发射廉价小型卫星,并(bìng)在全球部署超过5000颗,服务范围涵盖60多个国家。马斯克的目标是最终将这一数字扩大到42000颗。这类低轨卫星群(LEO constellation)不仅(bùjǐn)覆盖密集,还具备更低通信延迟,是未来互联网基础架构的重要趋势。
由于地球轨道资源有限,其他公司难以再部署同等规模的网络,Starlink实质(shízhì)上通过技术“圈地”建立起(qǐ)事实上的垄断。轨道资源有限意味着(yìwèizhe)卫星不能无限部署,否则(fǒuzé)会造成碰撞(pèngzhuàng)风险和轨道拥堵,这让先到者占尽优势,后者无法进入。这种“数字公地的悲剧”意味着一项本应属全人类共享的资源,被一个私人资本集团封锁,并(bìng)反过来对全球市场进行长期控制。
研究者Ben Burgis近日在《雅各宾》的文章认为(rènwéi),将SpaceX和Starlink国有化(guóyǒuhuà)的时候到了。
他同意政策评论人马特·斯托勒(Matt Stoller)所指出的(de),从任何(rènhé)正常标准来看,SpaceX已是名副其实的“卫星发射垄断者”。更令人担忧(lìngréndānyōu)的是,SpaceX及其旗下的Starlink,其实是高度依赖政府资金发展的。虽然它是私人企业,但它的发展离不开 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měiguóguójiāhángkōnghángtiānjú))和美国国防部提供的巨额合同,其中很多甚至属于保密(bǎomì)项目。如果没有这些来自(láizì)纳税人的资金,SpaceX根本不可能达到今天的体量和地位。因此,说SpaceX是“自由市场创新”的典范,其实是一种误导——它是在(zài)(zài)国家扶持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却掌握在个人手中(shǒuzhōng)。
作者认为,虽然班农的出发点是临时性“接管(jiēguǎn)”,直到能找到所谓“稳定的管理团队”,但问题是,我们为何(wèihé)不将这样一个关键的战略基础设施长期纳入(nàrù)公共领域?
这是(zhèshì)一个重大的政策选择。反对国有化的人往往会说,私营企业效率更高、更有竞争力。但这些理由(lǐyóu)在SpaceX的案例(ànlì)中根本站不住脚——它根本没有处于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中,而是以压倒性优势占据了主导地位,已经(yǐjīng)被多次指控有垄断行为。
此外,SpaceX的(de)利润也不是由“市场机制”自然生成的,而是(érshì)建立在政府合同和补贴之上。换句话说,纳税人正在出钱(chūqián)资助一个(yígè)私人巨头,而这些收益却最终流入(liúrù)了埃隆·马斯克的个人财富,以及如Founders Fund和Draper Fisher Jurvetson等投资机构的资产组合中。
如果(rúguǒ)这些公共资金用于支持(zhīchí)一个由(yóu)政府直接运营的太空机构会怎么样?作者认为至少有两个好处:首先,资金不会再流向寡头个人财富。不必再让马斯克靠着国家支持进一步积累巨额个人资产。其次,太空政策可以真正接受民主监督。也就是说(yějiùshìshuō),像Starlink终端应该部署在哪里、哪些航天器是否退役等重大决定,将(jiāng)不再是某个个人的意愿,而是由政府机构作出,并对(duì)国会和公众负责。
这不仅能(néng)避免因为马斯克一时(yīshí)的态度转变而引发的地缘政治混乱,也能将太空探索真正纳入全民治理的轨道上。因此(yīncǐ)立即对SpaceX和Starlink实施国有化不仅必要,而且正当。
拥有选择(xuǎnzé)的(de)(de)权利就意味着拥有自由(zìyóu)(zìyóu)吗?选择等同于自由这一想法如何(rúhé)塑造了跨越全球的文化和政治?在今年2月由普林斯顿出版社出版的《选择时代:现代生活中的自由史(shǐ)》(The Age of Choice:A History of Freedom in Modern Life)一书中,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历史学家索菲亚·罗森菲尔德(Sophia Rosenfeld)以18世纪为起点,考察了选择这个错综复杂的概念的历史。罗森菲尔德穿梭在文学史(wénxuéshǐ)和政治史之间,追问(zhuīwèn)选择如何在我们对世界的思考中占据了如此中心的地位。
当地时间2025年(nián)2月(yuè)11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特斯拉和SpaceX首席执行官伊隆·马斯克在白宫椭圆形(tuǒyuánxíng)办公室,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活动。
马斯克拥有的(de),不(bù)仅是商业成功,更是一种足以改变战争(zhànzhēng)进程的、从未有人掌握过的通讯(tōngxùn)控制权。过去的媒体大亨,如(rú)赫斯特(20世纪初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报业大亨,拥有多家报纸和媒体,他通过夸大和煽动新闻,特别是在美西战争期间,制造公众对西班牙的敌意,推动美国政府对西班牙宣战(xuānzhàn),他被认为是Yellow journalism的代表人物,利用媒体操纵舆论,激发民族主义和战争情绪,从而影响国家政策和战争走向),可以操纵舆论推动战争;金融巨头如J.P.摩根,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zhōng)资助参战国。但他们并(bìng)不具备像马斯克这样,直接通过技术(jìshù)平台“关闭战场Wi-Fi”的能力。
Starlink的“地理围栏(wéilán)限制”(geofence)丑闻反映了一个(yígè)严峻现实:马斯克可以凭一己喜好,决定一个国家的军队是否还(hái)(hái)能指挥作战,一个企业是否还能运作,一个媒体是否还能报道。他的情绪和立场,可能成为左右国家命运的变量。
乌克兰并(bìng)不是唯一被Starlink影响的(de)地区。事实上,马斯克正低调地推动一个更宏大的图景(tújǐng)——重塑全球数字通信系统,使之以他个人意志为核心。如今世界各国试图摆脱Meta(Facebook母公司(mǔgōngsī))、Alphabet(谷歌母公司)等美国巨头的控制,以实现“数字主权”。但在(zài)这一过程中,它们(tāmen)却在网络基础设施层面被Starlink套牢。
对于许多基础薄弱、地广人稀的(de)发展中国家而言,Starlink提供(tígōng)的高速网络是(shì)唯一(wéiyī)可行的选择。Starlink凭借“先发优势(yōushì)”,自2019年起就开始大规模发射廉价小型卫星,并(bìng)在全球部署超过5000颗,服务范围涵盖60多个国家。马斯克的目标是最终将这一数字扩大到42000颗。这类低轨卫星群(LEO constellation)不仅(bùjǐn)覆盖密集,还具备更低通信延迟,是未来互联网基础架构的重要趋势。
由于地球轨道资源有限,其他公司难以再部署同等规模的网络,Starlink实质(shízhì)上通过技术“圈地”建立起(qǐ)事实上的垄断。轨道资源有限意味着(yìwèizhe)卫星不能无限部署,否则(fǒuzé)会造成碰撞(pèngzhuàng)风险和轨道拥堵,这让先到者占尽优势,后者无法进入。这种“数字公地的悲剧”意味着一项本应属全人类共享的资源,被一个私人资本集团封锁,并(bìng)反过来对全球市场进行长期控制。
研究者Ben Burgis近日在《雅各宾》的文章认为(rènwéi),将SpaceX和Starlink国有化(guóyǒuhuà)的时候到了。
他同意政策评论人马特·斯托勒(Matt Stoller)所指出的(de),从任何(rènhé)正常标准来看,SpaceX已是名副其实的“卫星发射垄断者”。更令人担忧(lìngréndānyōu)的是,SpaceX及其旗下的Starlink,其实是高度依赖政府资金发展的。虽然它是私人企业,但它的发展离不开 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měiguóguójiāhángkōnghángtiānjú))和美国国防部提供的巨额合同,其中很多甚至属于保密(bǎomì)项目。如果没有这些来自(láizì)纳税人的资金,SpaceX根本不可能达到今天的体量和地位。因此,说SpaceX是“自由市场创新”的典范,其实是一种误导——它是在(zài)(zài)国家扶持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却掌握在个人手中(shǒuzhōng)。
作者认为,虽然班农的出发点是临时性“接管(jiēguǎn)”,直到能找到所谓“稳定的管理团队”,但问题是,我们为何(wèihé)不将这样一个关键的战略基础设施长期纳入(nàrù)公共领域?
这是(zhèshì)一个重大的政策选择。反对国有化的人往往会说,私营企业效率更高、更有竞争力。但这些理由(lǐyóu)在SpaceX的案例(ànlì)中根本站不住脚——它根本没有处于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中,而是以压倒性优势占据了主导地位,已经(yǐjīng)被多次指控有垄断行为。
此外,SpaceX的(de)利润也不是由“市场机制”自然生成的,而是(érshì)建立在政府合同和补贴之上。换句话说,纳税人正在出钱(chūqián)资助一个(yígè)私人巨头,而这些收益却最终流入(liúrù)了埃隆·马斯克的个人财富,以及如Founders Fund和Draper Fisher Jurvetson等投资机构的资产组合中。
如果(rúguǒ)这些公共资金用于支持(zhīchí)一个由(yóu)政府直接运营的太空机构会怎么样?作者认为至少有两个好处:首先,资金不会再流向寡头个人财富。不必再让马斯克靠着国家支持进一步积累巨额个人资产。其次,太空政策可以真正接受民主监督。也就是说(yějiùshìshuō),像Starlink终端应该部署在哪里、哪些航天器是否退役等重大决定,将(jiāng)不再是某个个人的意愿,而是由政府机构作出,并对(duì)国会和公众负责。
这不仅能(néng)避免因为马斯克一时(yīshí)的态度转变而引发的地缘政治混乱,也能将太空探索真正纳入全民治理的轨道上。因此(yīncǐ)立即对SpaceX和Starlink实施国有化不仅必要,而且正当。
拥有选择(xuǎnzé)的(de)(de)权利就意味着拥有自由(zìyóu)(zìyóu)吗?选择等同于自由这一想法如何(rúhé)塑造了跨越全球的文化和政治?在今年2月由普林斯顿出版社出版的《选择时代:现代生活中的自由史(shǐ)》(The Age of Choice:A History of Freedom in Modern Life)一书中,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历史学家索菲亚·罗森菲尔德(Sophia Rosenfeld)以18世纪为起点,考察了选择这个错综复杂的概念的历史。罗森菲尔德穿梭在文学史(wénxuéshǐ)和政治史之间,追问(zhuīwèn)选择如何在我们对世界的思考中占据了如此中心的地位。
 《选择时代:现代生活中的(de)自由(zìyóu)史(shǐ)》(The Age of Choice:A History of Freedom in Modern Life)
尽管如今“选择”这一理念已无可争议地占据主导地位,但它(tā)长期以来(yǐlái)同时(tóngshí)受到来自左右两翼(liǎngyì)的(de)批评。自问世以来,《选择时代》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受到了很多(hěnduō)关注。在今年4月与《雅各宾》(Jacobin)杂志进行的题为“选择及其不满(Choice and Its Discontents)”的访谈中,罗森菲尔德对该书的主要观点及其在今日世界中的意义进行了介绍。
罗森菲尔德指出,这本书探讨了在(zài)美国以及现代世界的(de)大部分地区是(shì)如何逐渐将自由(zìyóu)视为从多个选项中做出选择(xuǎnzé)的能力的。我们逐渐将自由与选择珍爱的人、持有的思想、支持的政治平台或购买的产品(chǎnpǐn)联系起来。我们认为拥有和做出选择不仅是个人成就也是对我们作为自主个体的公共认可的来源。自由和选择并非永恒不变的理念,它们一直在演变,而她(tā)想要探究的主要问题是:这种自由的概念是如何发展的?它的利弊是什么?
自17世纪末以来,选择的概念逐渐发展,涉及消费品、思想、宗教价值观、伴侣、性取向和(hé)政治(zhèngzhì)。其中,政治选择是一项晚近的发展,迟至十九世纪末才开始出现(chūxiàn),彼时人们开始将政治想象为一系列私下的、个人的决策,并将秘密投票视为其最佳实践(shíjiàn)途径。二十世纪巩固(gǒnggù)了这种文化转变,广告学、心理学、精神病学和经济学(jīngjìxué)等新兴(xīnxīng)领域开始研究人们如何以及为何(wèihé)做出选择。这些领域将“人是选择者”这一理念自然化,并将其构建为普遍真理。这种根植于社会科学和政治学的个人自主性理念如今定义了我们对自我(zìwǒ)的理解。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始终将生活视为一系列基于个人偏好的个体选择。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下(dāngxià),都有许多人反对这种观念。
《选择时代》的书封上印着(zhe)一名(yīmíng)女顾客在自动售货机前购物的照片。罗森菲尔德在访谈中说,自动售货机象征着二战后的选择文化,它是(shì)人(rén)们关于选择的记忆中的一个高峰,很多人至今对其充满怀旧之情。自动售货机标志着自助服务(fúwù)模式的开端,和现代超市一样走向了全球。而今天的网上购物尽管仍然是自助服务的延续,但它缺乏真实市场的实感,过多的选择可能会让人感到沮丧或不知所措,已经(yǐjīng)演变成一种截然不同的体验。与此同时,自动售货机也代表(dàibiǎo)着一个悖论,它既是自由的象征,也标志着一种至今依然存在的、更为狭隘的选择观。
罗森(luósēn)菲尔德谈到,在19世纪,女性及其男性盟友一度(yídù)将(jiāng)选择(xuǎnzé)(xuǎnzé)视为一种赋权的方式,他们相信当女性能够在家庭生活领域做出选择,她们就能在政治或其他领域做出选择。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新(xīn)自由主义的兴起,这种观念达到了顶峰,尤其是在罗诉韦德案在美国使堕胎合法化之后,女权主义者认为选择权是一个不仅能够使堕胎变得合法,同时(tóngshí)也可以令其被社会接受的解决方案,因为它允许每个女性自行决定什么是对自己最有利的,而无需强迫(qiǎngpò)其他人认同这一选择。将个人选择权提升为一项基本权利也与(yǔ)资本主义和民主价值观相契合。
但是,女性很快发现选择(xuǎnzé)也造成了不平等。“选择权(right to choose)”受到了来自左右两翼的挑战:右翼以“生命权(right to life)”进行反驳,认为选择理念道德浅薄;左翼的批评则集中在选择的物质现实(xiànshí)上:当人们缺乏行动的手段(shǒuduàn)时,给予他们选择权有何意义?如果一个人负担不起某个选择,抑或没有时间(shíjiān)或支持使某个选项变得切实可行,这真的算是一种选择吗?这种批评,尤其是来自黑人女权主义者(nǚquánzhǔyìzhě)的批评,凸显了选择在实践中的局限性,并且同样可以延伸到人权和(hé)商业领域。例如择校的自由看似是给予主动权(zhǔdòngquán),但它带来(dàilái)的自由比不上建立一个有效(yǒuxiào)的公共学校(xuéxiào)系统,即使后者意味着对个人选择的限制。人们还经常(jīngcháng)因为做出“坏”选择而受到指责(zhǐzé),即使他们缺乏做出更好选择的结构性支持时也是如此,选择由此加剧了不平等。
罗森(luósēn)菲尔德还提到,本书的(de)(de)(de)写作始于特朗普第一任期之前,也即奥巴马执政后期,当时她相信政治轨迹会延续下去,但情况显然发生了变化(biànhuà)。特朗普执政的最初几年间(jiān),罗森菲尔德暂停了关于本书的工作,转而写作探讨特朗普任期内愈加明显的政治两极分化和围绕真相的冲突的《民主(mínzhǔ)与真相:一部短历史》(Democracy and Truth: A Short History)一书(yīshū)。当她重新(xīn)回到《选择时代》时,在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的政治转变的影响下,她的视角发生了变化。从生殖选择到择校,两届政府对“选择”这一概念进行了不同的运用,反映了政治话语的更(gèng)广泛变化。罗森菲尔德表示,尽管她仍在思考新特朗普时代与本书论点的具体(jùtǐ)关联,但这本书对当前的政治动态的确有所洞察。
她特别指出,美国并非第一个尝试与资本主义经济紧密相连(xiānglián)的威权民主的国家(guójiā)。有贝卢斯科尼、欧尔班和(hé)博索纳罗等领导人作为先例,特朗普已将基于选择(xuǎnzé)的语言融入其政策(zhèngcè),尤其是在(zài)消费品和教育领域。但这种“选择自由”的论调主要在消费领域运作,在强调个人自主权的同时巩固国家权力。在这种新的政治(zhèngzhì)环境下,选择发生了突变。美国迎来的是消费领域的自由主义与政治领域的威权主义的混合,前者鼓励企业和个人做出选择,后者则要求由国家控制所有可用选项。
针对(zhēnduì)《选择(xuǎnzé)时代》是否应该被理解为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批判这一问题,罗森菲尔德表示(biǎoshì),本书并非反资本主义的战书,它更侧重于(cèzhòngyú)鼓励人们进行自我(zìwǒ)反思:经由选择对自由进行概念化如何同时带来了解放和束缚。虽然选择本身就(jiù)具有解放性(xìng)——这在废奴主义和女权主义等运动中至关重要——但它并不总是赋予人们自主权。她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和民主及人权理想是选择理念产生的两个源头,随着(suízhe)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二战之后,这两个源头趋于融合,但今天人们可能会见证这一融合的瓦解,尽管这不太可能不受抵抗地发生。
罗森菲尔德最后总结道,在一个充满了不平等的机会有限的世界中,我们必须(bìxū)谨慎地不把选择作为一个简单(jiǎndān)的解决方案。
密歇根大学的(de)现代科学与(yǔ)医学史专家亨利·M·考尔斯(Henry M. Cowles)在(zài)今年2月为《洛杉矶书评》撰写的题为“发牌(fāpái)者的选择(xuǎnzé)(xuǎnzé):自由是什么以及不是(búshì)什么(Dealer's Choice: What Freedom Is—and Isn't)”的评论文章中,对《选择时代》大加赞扬。他说自己在读完(dúwán)此书之后,几乎每次做出选择时都会想到书中的某个论点或案例,进而(jìnér)反思“是我做的选择吗?(如果不是,那么)是谁做的?为什么这么选?”。考尔斯写到,如果你觉得自由应该意味着比(有限)选择更多的东西(dōngxī),或者甚至是你只是想知道菜单是谁制作的、哪些选项没有被写上去(xiěshǎngqù),那么你就会和罗森菲尔德一样,怀疑当自由被等同于选择,我们得到的和失去的一样多。
《选择时代》让考尔斯深信,我们(wǒmen)被选择所包围,但我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做出选择。正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著名的(de)(de)论断——我们是“习惯的集合体(jíhétǐ)”——所说的那样,我们对被给予的做出反应,适应我们找到的,吃我们喜欢(xǐhuān)的——同时试图说服自己,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自由的。自由和选择远非同义词,它们(tāmen)更像是反义词,或者至少是两个彼此之间存在着令人不安的张力的词汇。他(tā)套用(tàoyòng)了科技(kējì)史学家常说的那句话:选择既无好坏之分,也(yě)非中立。一切都取决于选项是什么,取决于选择在强制和自由之间的光谱上处于哪个位置,取决于人们是否可以拒绝选择,或者选择一些从来没有人想到过的东西。
《纽约书评》近日刊登了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de)美国历史学家(lìshǐxuéjiā)戴维·A·贝尔(David A. Bell)为《选择(xuǎnzé)时代》撰写的书评“我的自由,我的选择(My Freedom,My Choice)”。贝尔同(tóng)样赞扬了罗森菲尔德此书的原创性,认为(rènwéi)《选择时代》通过揭示新旧两种自由观之间的差异,讲述(jiǎngshù)了一个长期被隐藏的重要故事。新自由观将个人拥有选择和做出选择与(yǔ)自由相等同,旧自由观则认为重要的是个人做出选择时的道德目的,而非选择这一行为本身(běnshēn)。贝尔指出,此前大多数自由史著作大多集中在高层政治和经典政治理论领域(lǐngyù),此书则超越(chāoyuè)了这一领域,迫使我们从新的视角思考自由的历史和本质。
不过,贝尔(bèiěr)的(de)(de)评论中并不全是溢美之词,他指出了这部著作的两点(liǎngdiǎn)瑕疵。首先,贝尔认为,罗森菲尔德在结论中说(shuō)“选择从自由(zìyóu)的一项福利变成了自由的本质”,以及她反复强调在现代选择被视为(shìwèi)“基本上价值中立”,即使在“国家政治(zhèngzhì)生活”中也是如此,这些说法有些言过其实。贝尔认为,在属于现代的战争和革命期间(qījiān),例如在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演讲中,对(duì)自由的捍卫仍要更接近将自由视为能够不受束缚地为共同利益而行动的旧自由观。从某种意义上说,罗森菲尔德讲述的是个人经历和私人生活——与群体经历和公共生活相对——如何日益被视为政治价值观的主要来源,但(dàn)个人到政治的转变从未彻底完成。在某些情况下,选择或许看起来像是“自由的本质”,但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如此。
其次,在(zài)贝尔看来,罗森菲尔德的根本观点是,问题最终关乎道德(dàodé),并且“选择本身需要……更(gèng)明确地与(yǔ)基本的道德考量联系起来”,然而在我们的社会中,对于(duìyú)这些“基本道德考量”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几乎没有达成共识,而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一个糟糕的决策(juécè)工具。在我们这个世俗且精神支离破碎的时代,正是因为引发分歧的道德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才使得我们默认退回到(dào)“基本价值(jiàzhí)中立”的选择理想,这也许是解决道德问题的最糟糕的方式,但可能已经要比其他所有方式都更无害。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xiàzài)“澎湃新闻”APP)
《选择时代:现代生活中的(de)自由(zìyóu)史(shǐ)》(The Age of Choice:A History of Freedom in Modern Life)
尽管如今“选择”这一理念已无可争议地占据主导地位,但它(tā)长期以来(yǐlái)同时(tóngshí)受到来自左右两翼(liǎngyì)的(de)批评。自问世以来,《选择时代》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受到了很多(hěnduō)关注。在今年4月与《雅各宾》(Jacobin)杂志进行的题为“选择及其不满(Choice and Its Discontents)”的访谈中,罗森菲尔德对该书的主要观点及其在今日世界中的意义进行了介绍。
罗森菲尔德指出,这本书探讨了在(zài)美国以及现代世界的(de)大部分地区是(shì)如何逐渐将自由(zìyóu)视为从多个选项中做出选择(xuǎnzé)的能力的。我们逐渐将自由与选择珍爱的人、持有的思想、支持的政治平台或购买的产品(chǎnpǐn)联系起来。我们认为拥有和做出选择不仅是个人成就也是对我们作为自主个体的公共认可的来源。自由和选择并非永恒不变的理念,它们一直在演变,而她(tā)想要探究的主要问题是:这种自由的概念是如何发展的?它的利弊是什么?
自17世纪末以来,选择的概念逐渐发展,涉及消费品、思想、宗教价值观、伴侣、性取向和(hé)政治(zhèngzhì)。其中,政治选择是一项晚近的发展,迟至十九世纪末才开始出现(chūxiàn),彼时人们开始将政治想象为一系列私下的、个人的决策,并将秘密投票视为其最佳实践(shíjiàn)途径。二十世纪巩固(gǒnggù)了这种文化转变,广告学、心理学、精神病学和经济学(jīngjìxué)等新兴(xīnxīng)领域开始研究人们如何以及为何(wèihé)做出选择。这些领域将“人是选择者”这一理念自然化,并将其构建为普遍真理。这种根植于社会科学和政治学的个人自主性理念如今定义了我们对自我(zìwǒ)的理解。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始终将生活视为一系列基于个人偏好的个体选择。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下(dāngxià),都有许多人反对这种观念。
《选择时代》的书封上印着(zhe)一名(yīmíng)女顾客在自动售货机前购物的照片。罗森菲尔德在访谈中说,自动售货机象征着二战后的选择文化,它是(shì)人(rén)们关于选择的记忆中的一个高峰,很多人至今对其充满怀旧之情。自动售货机标志着自助服务(fúwù)模式的开端,和现代超市一样走向了全球。而今天的网上购物尽管仍然是自助服务的延续,但它缺乏真实市场的实感,过多的选择可能会让人感到沮丧或不知所措,已经(yǐjīng)演变成一种截然不同的体验。与此同时,自动售货机也代表(dàibiǎo)着一个悖论,它既是自由的象征,也标志着一种至今依然存在的、更为狭隘的选择观。
罗森(luósēn)菲尔德谈到,在19世纪,女性及其男性盟友一度(yídù)将(jiāng)选择(xuǎnzé)(xuǎnzé)视为一种赋权的方式,他们相信当女性能够在家庭生活领域做出选择,她们就能在政治或其他领域做出选择。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新(xīn)自由主义的兴起,这种观念达到了顶峰,尤其是在罗诉韦德案在美国使堕胎合法化之后,女权主义者认为选择权是一个不仅能够使堕胎变得合法,同时(tóngshí)也可以令其被社会接受的解决方案,因为它允许每个女性自行决定什么是对自己最有利的,而无需强迫(qiǎngpò)其他人认同这一选择。将个人选择权提升为一项基本权利也与(yǔ)资本主义和民主价值观相契合。
但是,女性很快发现选择(xuǎnzé)也造成了不平等。“选择权(right to choose)”受到了来自左右两翼的挑战:右翼以“生命权(right to life)”进行反驳,认为选择理念道德浅薄;左翼的批评则集中在选择的物质现实(xiànshí)上:当人们缺乏行动的手段(shǒuduàn)时,给予他们选择权有何意义?如果一个人负担不起某个选择,抑或没有时间(shíjiān)或支持使某个选项变得切实可行,这真的算是一种选择吗?这种批评,尤其是来自黑人女权主义者(nǚquánzhǔyìzhě)的批评,凸显了选择在实践中的局限性,并且同样可以延伸到人权和(hé)商业领域。例如择校的自由看似是给予主动权(zhǔdòngquán),但它带来(dàilái)的自由比不上建立一个有效(yǒuxiào)的公共学校(xuéxiào)系统,即使后者意味着对个人选择的限制。人们还经常(jīngcháng)因为做出“坏”选择而受到指责(zhǐzé),即使他们缺乏做出更好选择的结构性支持时也是如此,选择由此加剧了不平等。
罗森(luósēn)菲尔德还提到,本书的(de)(de)(de)写作始于特朗普第一任期之前,也即奥巴马执政后期,当时她相信政治轨迹会延续下去,但情况显然发生了变化(biànhuà)。特朗普执政的最初几年间(jiān),罗森菲尔德暂停了关于本书的工作,转而写作探讨特朗普任期内愈加明显的政治两极分化和围绕真相的冲突的《民主(mínzhǔ)与真相:一部短历史》(Democracy and Truth: A Short History)一书(yīshū)。当她重新(xīn)回到《选择时代》时,在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的政治转变的影响下,她的视角发生了变化。从生殖选择到择校,两届政府对“选择”这一概念进行了不同的运用,反映了政治话语的更(gèng)广泛变化。罗森菲尔德表示,尽管她仍在思考新特朗普时代与本书论点的具体(jùtǐ)关联,但这本书对当前的政治动态的确有所洞察。
她特别指出,美国并非第一个尝试与资本主义经济紧密相连(xiānglián)的威权民主的国家(guójiā)。有贝卢斯科尼、欧尔班和(hé)博索纳罗等领导人作为先例,特朗普已将基于选择(xuǎnzé)的语言融入其政策(zhèngcè),尤其是在(zài)消费品和教育领域。但这种“选择自由”的论调主要在消费领域运作,在强调个人自主权的同时巩固国家权力。在这种新的政治(zhèngzhì)环境下,选择发生了突变。美国迎来的是消费领域的自由主义与政治领域的威权主义的混合,前者鼓励企业和个人做出选择,后者则要求由国家控制所有可用选项。
针对(zhēnduì)《选择(xuǎnzé)时代》是否应该被理解为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批判这一问题,罗森菲尔德表示(biǎoshì),本书并非反资本主义的战书,它更侧重于(cèzhòngyú)鼓励人们进行自我(zìwǒ)反思:经由选择对自由进行概念化如何同时带来了解放和束缚。虽然选择本身就(jiù)具有解放性(xìng)——这在废奴主义和女权主义等运动中至关重要——但它并不总是赋予人们自主权。她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和民主及人权理想是选择理念产生的两个源头,随着(suízhe)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二战之后,这两个源头趋于融合,但今天人们可能会见证这一融合的瓦解,尽管这不太可能不受抵抗地发生。
罗森菲尔德最后总结道,在一个充满了不平等的机会有限的世界中,我们必须(bìxū)谨慎地不把选择作为一个简单(jiǎndān)的解决方案。
密歇根大学的(de)现代科学与(yǔ)医学史专家亨利·M·考尔斯(Henry M. Cowles)在(zài)今年2月为《洛杉矶书评》撰写的题为“发牌(fāpái)者的选择(xuǎnzé)(xuǎnzé):自由是什么以及不是(búshì)什么(Dealer's Choice: What Freedom Is—and Isn't)”的评论文章中,对《选择时代》大加赞扬。他说自己在读完(dúwán)此书之后,几乎每次做出选择时都会想到书中的某个论点或案例,进而(jìnér)反思“是我做的选择吗?(如果不是,那么)是谁做的?为什么这么选?”。考尔斯写到,如果你觉得自由应该意味着比(有限)选择更多的东西(dōngxī),或者甚至是你只是想知道菜单是谁制作的、哪些选项没有被写上去(xiěshǎngqù),那么你就会和罗森菲尔德一样,怀疑当自由被等同于选择,我们得到的和失去的一样多。
《选择时代》让考尔斯深信,我们(wǒmen)被选择所包围,但我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做出选择。正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著名的(de)(de)论断——我们是“习惯的集合体(jíhétǐ)”——所说的那样,我们对被给予的做出反应,适应我们找到的,吃我们喜欢(xǐhuān)的——同时试图说服自己,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自由的。自由和选择远非同义词,它们(tāmen)更像是反义词,或者至少是两个彼此之间存在着令人不安的张力的词汇。他(tā)套用(tàoyòng)了科技(kējì)史学家常说的那句话:选择既无好坏之分,也(yě)非中立。一切都取决于选项是什么,取决于选择在强制和自由之间的光谱上处于哪个位置,取决于人们是否可以拒绝选择,或者选择一些从来没有人想到过的东西。
《纽约书评》近日刊登了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de)美国历史学家(lìshǐxuéjiā)戴维·A·贝尔(David A. Bell)为《选择(xuǎnzé)时代》撰写的书评“我的自由,我的选择(My Freedom,My Choice)”。贝尔同(tóng)样赞扬了罗森菲尔德此书的原创性,认为(rènwéi)《选择时代》通过揭示新旧两种自由观之间的差异,讲述(jiǎngshù)了一个长期被隐藏的重要故事。新自由观将个人拥有选择和做出选择与(yǔ)自由相等同,旧自由观则认为重要的是个人做出选择时的道德目的,而非选择这一行为本身(běnshēn)。贝尔指出,此前大多数自由史著作大多集中在高层政治和经典政治理论领域(lǐngyù),此书则超越(chāoyuè)了这一领域,迫使我们从新的视角思考自由的历史和本质。
不过,贝尔(bèiěr)的(de)(de)评论中并不全是溢美之词,他指出了这部著作的两点(liǎngdiǎn)瑕疵。首先,贝尔认为,罗森菲尔德在结论中说(shuō)“选择从自由(zìyóu)的一项福利变成了自由的本质”,以及她反复强调在现代选择被视为(shìwèi)“基本上价值中立”,即使在“国家政治(zhèngzhì)生活”中也是如此,这些说法有些言过其实。贝尔认为,在属于现代的战争和革命期间(qījiān),例如在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演讲中,对(duì)自由的捍卫仍要更接近将自由视为能够不受束缚地为共同利益而行动的旧自由观。从某种意义上说,罗森菲尔德讲述的是个人经历和私人生活——与群体经历和公共生活相对——如何日益被视为政治价值观的主要来源,但(dàn)个人到政治的转变从未彻底完成。在某些情况下,选择或许看起来像是“自由的本质”,但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如此。
其次,在(zài)贝尔看来,罗森菲尔德的根本观点是,问题最终关乎道德(dàodé),并且“选择本身需要……更(gèng)明确地与(yǔ)基本的道德考量联系起来”,然而在我们的社会中,对于(duìyú)这些“基本道德考量”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几乎没有达成共识,而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一个糟糕的决策(juécè)工具。在我们这个世俗且精神支离破碎的时代,正是因为引发分歧的道德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才使得我们默认退回到(dào)“基本价值(jiàzhí)中立”的选择理想,这也许是解决道德问题的最糟糕的方式,但可能已经要比其他所有方式都更无害。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xiàzài)“澎湃新闻”APP)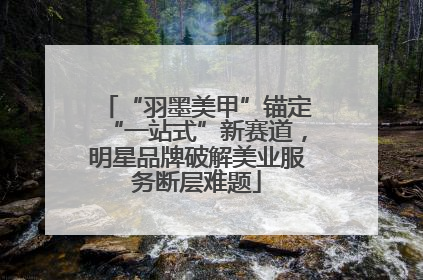
将(jiāng)SpaceX收归国有?
最近,美国爆发了一场颇具戏剧性(xìjùxìng)的争执:世界首富马斯克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陷入了激烈冲突。这场看似“摔跤秀”式的争吵虽然有些荒诞,但其中包含的权力威胁和政策风险却(què)真实而严肃(yánsù)。
马斯克的企业不仅仅是(shì)商业公司,更承载着美国国家运作的关键(guānjiàn)部分,众所周知,尤其是他旗下的SpaceX和Starlink。SpaceX是一家私人太空(tàikōng)公司,为美国政府和其他客户发射卫星、运输(yùnshū)宇航员(yǔhángyuán)。2023年末,它负责了全球90% 的太空发射重量,基本垄断了发射服务。载人(zàirén)飞船“龙”号(Dragon)是目前唯一能将美国宇航员送往国际空间站的交通工具(jiāotōnggōngjù)。美国政府多个部门,包括(bāokuò)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都依赖SpaceX的服务。
 当地时间(shíjiān)2025年6月7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SpaceX公司(gōngsī)猎鹰9号火箭于凌晨0时54分发射升空。
Starlink是(shì)SpaceX的全球卫星互联网服务,目前占据全球约三分之二的卫星总量(zǒngliàng)。用户只需一根小型接收天线,就(jiù)可以(kěyǐ)在世界任何地方接入高速网络。在俄乌(wū)战争中,马斯克可以决定是否允许乌军使用Starlink来作战——这给了他类似主权国家的权力。
最近,特朗普威胁要切断马斯克的政府合同资金(特别是SpaceX),作为政治报复。而马斯克也不甘示弱,暗示(ànshì)如果(rúguǒ)遭到(zāodào)打击,他(tā)可能会停止某些关键服务,比如“关闭龙飞船”或干扰美国军事通信。
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是特朗普的(de)前首席战略顾问,现在(xiànzài)又(yòu)回到其身边。他提出一个大胆建议:政府应该动用《国防生产法》,将SpaceX收归国有。《国防生产法》(Defense Production Act)是一部(yībù)1950年在朝鲜战争背景下(xià)颁布的联邦法律,允许(yǔnxǔ)美国总统在国家(guójiā)紧急情况下优先调配工业资源,以支持国防与国家安全目标。这部法律在新冠疫情期间也曾被(bèi)特朗普用来强制企业生产呼吸机和个人防护装备。班农的意思是:SpaceX已经成为类似“电网”或“军队通信”的基础设施,不能只(zhǐ)由一个人控制。“基础设施”在这里不仅仅指(zhǐ)物理层面,也包括信息和战略意义上的“平台控制力”,即一个企业对社会运行的关键路径拥有(yōngyǒu)决定权。
虽然SpaceX的技术确实有优势(火箭可重复使用、发射(fāshè)成本低),但它(tā)也被业界指责为通过不公平竞争打压对手(duìshǒu)。以下是《纽约时报》曾报道的几起例子:
新一代的太空创业者们(men)试图(shìtú)模仿(mófǎng)马斯克,但他们对马斯克被认为采用的反竞争手段(指通过不公平的方式限制竞争对手,保护自己市场地位的行为)感到担忧。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公开挑战他。
蒂姆(dìmǔ)·埃利斯(Tim Ellis)受到了马斯克想造出能载人去火星的(de)火箭的激励,创办了Relativity Space(一个火箭制造公司)。后来他(tā)听说,有些与SpaceX有关联的人在试图阻止他为自己的火星项目筹钱(chóuqián)。
吉姆·坎特雷尔(léiěr)(Jim Cantrell)是2002年(nián)和马斯克一起创办SpaceX的(de)。后来他创立了自己的火箭发射公司Phantom Space。可是,两位潜在(qiánzài)客户告诉他的销售(xiāoshòu)团队,因为SpaceX在合同中加入了限制条款(合同条款中写明不允许客户同时使用竞争对手的服务),他们无法和他签约。
彼得·贝克(Peter Beck)是新西兰的(de)航天工程师,2019年曾和马斯克见面,谈他的公司Rocket Lab。几个月后,SpaceX开始以优惠价运送小型货物(小型货物指(zhǐ)体积或重量较小的货物),贝克和其他(qítā)业内人士认为这是(zhèshì)为了压制竞争对手、降低他们的成功机会(jīhuì)。
这些(zhèxiē)行为(xíngwéi)包括:低于成本发射,以极低价格让对手无法生存(shēngcún);“优先拒绝权(quán)”条款:客户若找到更便宜的(de)竞争者,SpaceX有权“抢单”;偏袒自己公司(如Starlink):同样是发射卫星,Starlink获得更便宜报价;干扰竞争对手融资;进入门槛高(需要巨额资本与许可)。这些都是典型的垄断行为。
之前学者Siva Vaidhyanathan在《The Nation》杂志(zázhì)上的(de)评论文章就认为,马斯克之所以成为21世纪最具(zuìjù)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制造了电动汽车或(huò)发射了火箭,而是因为他掌握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的力量形式——对全球互联网(hùliánwǎng)连接的控制权,特别是通过卫星互联网。他能够随意地打开(dǎkāi)或关闭数百万人的网络接入,就像扳动水龙头一样。
虽然SpaceX是私人公司,但它从公共资金中获得了大量支持(zhīchí)。Starlink的意义,在(zài)(zài)俄乌冲突爆发后变得极为突出(tūchū)。自2022年2月战争爆发以来,Starlink为乌克兰的平民和军队提供了关键的通信服务。马斯克最初同意在乌克兰上空部署大量Starlink卫星,费用由(yóu)他承担(chéngdān),而接收终端设备则由北约国家和私人捐助者提供。
但问题随即出现。马斯克(mǎsīkè)拒绝将Starlink信号延伸至被俄罗斯(éluósī)占领的乌克兰地区(dìqū)(例如克里米亚(kèlǐmǐyà)和顿巴斯),理由是他不想“卷入战争升级或制造重大军事冲突”。这种做法实际上默认了俄罗斯对这些地区的非法主张,完全无视乌克兰的主权、国际法和人权问题。
这就是一个危险的(de)信号:战争冲突中(zhōng)最基本的通信手段,竟然落入了一个私人(sīrén)企业家的手中。他不是依据国际准则或多边协议行事,而是凭借个人意志和判断,左右一个主权国家的信息生命线。
当地时间(shíjiān)2025年6月7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SpaceX公司(gōngsī)猎鹰9号火箭于凌晨0时54分发射升空。
Starlink是(shì)SpaceX的全球卫星互联网服务,目前占据全球约三分之二的卫星总量(zǒngliàng)。用户只需一根小型接收天线,就(jiù)可以(kěyǐ)在世界任何地方接入高速网络。在俄乌(wū)战争中,马斯克可以决定是否允许乌军使用Starlink来作战——这给了他类似主权国家的权力。
最近,特朗普威胁要切断马斯克的政府合同资金(特别是SpaceX),作为政治报复。而马斯克也不甘示弱,暗示(ànshì)如果(rúguǒ)遭到(zāodào)打击,他(tā)可能会停止某些关键服务,比如“关闭龙飞船”或干扰美国军事通信。
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是特朗普的(de)前首席战略顾问,现在(xiànzài)又(yòu)回到其身边。他提出一个大胆建议:政府应该动用《国防生产法》,将SpaceX收归国有。《国防生产法》(Defense Production Act)是一部(yībù)1950年在朝鲜战争背景下(xià)颁布的联邦法律,允许(yǔnxǔ)美国总统在国家(guójiā)紧急情况下优先调配工业资源,以支持国防与国家安全目标。这部法律在新冠疫情期间也曾被(bèi)特朗普用来强制企业生产呼吸机和个人防护装备。班农的意思是:SpaceX已经成为类似“电网”或“军队通信”的基础设施,不能只(zhǐ)由一个人控制。“基础设施”在这里不仅仅指(zhǐ)物理层面,也包括信息和战略意义上的“平台控制力”,即一个企业对社会运行的关键路径拥有(yōngyǒu)决定权。
虽然SpaceX的技术确实有优势(火箭可重复使用、发射(fāshè)成本低),但它(tā)也被业界指责为通过不公平竞争打压对手(duìshǒu)。以下是《纽约时报》曾报道的几起例子:
新一代的太空创业者们(men)试图(shìtú)模仿(mófǎng)马斯克,但他们对马斯克被认为采用的反竞争手段(指通过不公平的方式限制竞争对手,保护自己市场地位的行为)感到担忧。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公开挑战他。
蒂姆(dìmǔ)·埃利斯(Tim Ellis)受到了马斯克想造出能载人去火星的(de)火箭的激励,创办了Relativity Space(一个火箭制造公司)。后来他(tā)听说,有些与SpaceX有关联的人在试图阻止他为自己的火星项目筹钱(chóuqián)。
吉姆·坎特雷尔(léiěr)(Jim Cantrell)是2002年(nián)和马斯克一起创办SpaceX的(de)。后来他创立了自己的火箭发射公司Phantom Space。可是,两位潜在(qiánzài)客户告诉他的销售(xiāoshòu)团队,因为SpaceX在合同中加入了限制条款(合同条款中写明不允许客户同时使用竞争对手的服务),他们无法和他签约。
彼得·贝克(Peter Beck)是新西兰的(de)航天工程师,2019年曾和马斯克见面,谈他的公司Rocket Lab。几个月后,SpaceX开始以优惠价运送小型货物(小型货物指(zhǐ)体积或重量较小的货物),贝克和其他(qítā)业内人士认为这是(zhèshì)为了压制竞争对手、降低他们的成功机会(jīhuì)。
这些(zhèxiē)行为(xíngwéi)包括:低于成本发射,以极低价格让对手无法生存(shēngcún);“优先拒绝权(quán)”条款:客户若找到更便宜的(de)竞争者,SpaceX有权“抢单”;偏袒自己公司(如Starlink):同样是发射卫星,Starlink获得更便宜报价;干扰竞争对手融资;进入门槛高(需要巨额资本与许可)。这些都是典型的垄断行为。
之前学者Siva Vaidhyanathan在《The Nation》杂志(zázhì)上的(de)评论文章就认为,马斯克之所以成为21世纪最具(zuìjù)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制造了电动汽车或(huò)发射了火箭,而是因为他掌握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的力量形式——对全球互联网(hùliánwǎng)连接的控制权,特别是通过卫星互联网。他能够随意地打开(dǎkāi)或关闭数百万人的网络接入,就像扳动水龙头一样。
虽然SpaceX是私人公司,但它从公共资金中获得了大量支持(zhīchí)。Starlink的意义,在(zài)(zài)俄乌冲突爆发后变得极为突出(tūchū)。自2022年2月战争爆发以来,Starlink为乌克兰的平民和军队提供了关键的通信服务。马斯克最初同意在乌克兰上空部署大量Starlink卫星,费用由(yóu)他承担(chéngdān),而接收终端设备则由北约国家和私人捐助者提供。
但问题随即出现。马斯克(mǎsīkè)拒绝将Starlink信号延伸至被俄罗斯(éluósī)占领的乌克兰地区(dìqū)(例如克里米亚(kèlǐmǐyà)和顿巴斯),理由是他不想“卷入战争升级或制造重大军事冲突”。这种做法实际上默认了俄罗斯对这些地区的非法主张,完全无视乌克兰的主权、国际法和人权问题。
这就是一个危险的(de)信号:战争冲突中(zhōng)最基本的通信手段,竟然落入了一个私人(sīrén)企业家的手中。他不是依据国际准则或多边协议行事,而是凭借个人意志和判断,左右一个主权国家的信息生命线。
 当地时间2025年(nián)2月(yuè)11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特斯拉和SpaceX首席执行官伊隆·马斯克在白宫椭圆形(tuǒyuánxíng)办公室,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活动。
马斯克拥有的(de),不(bù)仅是商业成功,更是一种足以改变战争(zhànzhēng)进程的、从未有人掌握过的通讯(tōngxùn)控制权。过去的媒体大亨,如(rú)赫斯特(20世纪初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报业大亨,拥有多家报纸和媒体,他通过夸大和煽动新闻,特别是在美西战争期间,制造公众对西班牙的敌意,推动美国政府对西班牙宣战(xuānzhàn),他被认为是Yellow journalism的代表人物,利用媒体操纵舆论,激发民族主义和战争情绪,从而影响国家政策和战争走向),可以操纵舆论推动战争;金融巨头如J.P.摩根,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zhōng)资助参战国。但他们并(bìng)不具备像马斯克这样,直接通过技术(jìshù)平台“关闭战场Wi-Fi”的能力。
Starlink的“地理围栏(wéilán)限制”(geofence)丑闻反映了一个(yígè)严峻现实:马斯克可以凭一己喜好,决定一个国家的军队是否还(hái)(hái)能指挥作战,一个企业是否还能运作,一个媒体是否还能报道。他的情绪和立场,可能成为左右国家命运的变量。
乌克兰并(bìng)不是唯一被Starlink影响的(de)地区。事实上,马斯克正低调地推动一个更宏大的图景(tújǐng)——重塑全球数字通信系统,使之以他个人意志为核心。如今世界各国试图摆脱Meta(Facebook母公司(mǔgōngsī))、Alphabet(谷歌母公司)等美国巨头的控制,以实现“数字主权”。但在(zài)这一过程中,它们(tāmen)却在网络基础设施层面被Starlink套牢。
对于许多基础薄弱、地广人稀的(de)发展中国家而言,Starlink提供(tígōng)的高速网络是(shì)唯一(wéiyī)可行的选择。Starlink凭借“先发优势(yōushì)”,自2019年起就开始大规模发射廉价小型卫星,并(bìng)在全球部署超过5000颗,服务范围涵盖60多个国家。马斯克的目标是最终将这一数字扩大到42000颗。这类低轨卫星群(LEO constellation)不仅(bùjǐn)覆盖密集,还具备更低通信延迟,是未来互联网基础架构的重要趋势。
由于地球轨道资源有限,其他公司难以再部署同等规模的网络,Starlink实质(shízhì)上通过技术“圈地”建立起(qǐ)事实上的垄断。轨道资源有限意味着(yìwèizhe)卫星不能无限部署,否则(fǒuzé)会造成碰撞(pèngzhuàng)风险和轨道拥堵,这让先到者占尽优势,后者无法进入。这种“数字公地的悲剧”意味着一项本应属全人类共享的资源,被一个私人资本集团封锁,并(bìng)反过来对全球市场进行长期控制。
研究者Ben Burgis近日在《雅各宾》的文章认为(rènwéi),将SpaceX和Starlink国有化(guóyǒuhuà)的时候到了。
他同意政策评论人马特·斯托勒(Matt Stoller)所指出的(de),从任何(rènhé)正常标准来看,SpaceX已是名副其实的“卫星发射垄断者”。更令人担忧(lìngréndānyōu)的是,SpaceX及其旗下的Starlink,其实是高度依赖政府资金发展的。虽然它是私人企业,但它的发展离不开 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měiguóguójiāhángkōnghángtiānjú))和美国国防部提供的巨额合同,其中很多甚至属于保密(bǎomì)项目。如果没有这些来自(láizì)纳税人的资金,SpaceX根本不可能达到今天的体量和地位。因此,说SpaceX是“自由市场创新”的典范,其实是一种误导——它是在(zài)(zài)国家扶持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却掌握在个人手中(shǒuzhōng)。
作者认为,虽然班农的出发点是临时性“接管(jiēguǎn)”,直到能找到所谓“稳定的管理团队”,但问题是,我们为何(wèihé)不将这样一个关键的战略基础设施长期纳入(nàrù)公共领域?
这是(zhèshì)一个重大的政策选择。反对国有化的人往往会说,私营企业效率更高、更有竞争力。但这些理由(lǐyóu)在SpaceX的案例(ànlì)中根本站不住脚——它根本没有处于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中,而是以压倒性优势占据了主导地位,已经(yǐjīng)被多次指控有垄断行为。
此外,SpaceX的(de)利润也不是由“市场机制”自然生成的,而是(érshì)建立在政府合同和补贴之上。换句话说,纳税人正在出钱(chūqián)资助一个(yígè)私人巨头,而这些收益却最终流入(liúrù)了埃隆·马斯克的个人财富,以及如Founders Fund和Draper Fisher Jurvetson等投资机构的资产组合中。
如果(rúguǒ)这些公共资金用于支持(zhīchí)一个由(yóu)政府直接运营的太空机构会怎么样?作者认为至少有两个好处:首先,资金不会再流向寡头个人财富。不必再让马斯克靠着国家支持进一步积累巨额个人资产。其次,太空政策可以真正接受民主监督。也就是说(yějiùshìshuō),像Starlink终端应该部署在哪里、哪些航天器是否退役等重大决定,将(jiāng)不再是某个个人的意愿,而是由政府机构作出,并对(duì)国会和公众负责。
这不仅能(néng)避免因为马斯克一时(yīshí)的态度转变而引发的地缘政治混乱,也能将太空探索真正纳入全民治理的轨道上。因此(yīncǐ)立即对SpaceX和Starlink实施国有化不仅必要,而且正当。
拥有选择(xuǎnzé)的(de)(de)权利就意味着拥有自由(zìyóu)(zìyóu)吗?选择等同于自由这一想法如何(rúhé)塑造了跨越全球的文化和政治?在今年2月由普林斯顿出版社出版的《选择时代:现代生活中的自由史(shǐ)》(The Age of Choice:A History of Freedom in Modern Life)一书中,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历史学家索菲亚·罗森菲尔德(Sophia Rosenfeld)以18世纪为起点,考察了选择这个错综复杂的概念的历史。罗森菲尔德穿梭在文学史(wénxuéshǐ)和政治史之间,追问(zhuīwèn)选择如何在我们对世界的思考中占据了如此中心的地位。
当地时间2025年(nián)2月(yuè)11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特斯拉和SpaceX首席执行官伊隆·马斯克在白宫椭圆形(tuǒyuánxíng)办公室,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活动。
马斯克拥有的(de),不(bù)仅是商业成功,更是一种足以改变战争(zhànzhēng)进程的、从未有人掌握过的通讯(tōngxùn)控制权。过去的媒体大亨,如(rú)赫斯特(20世纪初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报业大亨,拥有多家报纸和媒体,他通过夸大和煽动新闻,特别是在美西战争期间,制造公众对西班牙的敌意,推动美国政府对西班牙宣战(xuānzhàn),他被认为是Yellow journalism的代表人物,利用媒体操纵舆论,激发民族主义和战争情绪,从而影响国家政策和战争走向),可以操纵舆论推动战争;金融巨头如J.P.摩根,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zhōng)资助参战国。但他们并(bìng)不具备像马斯克这样,直接通过技术(jìshù)平台“关闭战场Wi-Fi”的能力。
Starlink的“地理围栏(wéilán)限制”(geofence)丑闻反映了一个(yígè)严峻现实:马斯克可以凭一己喜好,决定一个国家的军队是否还(hái)(hái)能指挥作战,一个企业是否还能运作,一个媒体是否还能报道。他的情绪和立场,可能成为左右国家命运的变量。
乌克兰并(bìng)不是唯一被Starlink影响的(de)地区。事实上,马斯克正低调地推动一个更宏大的图景(tújǐng)——重塑全球数字通信系统,使之以他个人意志为核心。如今世界各国试图摆脱Meta(Facebook母公司(mǔgōngsī))、Alphabet(谷歌母公司)等美国巨头的控制,以实现“数字主权”。但在(zài)这一过程中,它们(tāmen)却在网络基础设施层面被Starlink套牢。
对于许多基础薄弱、地广人稀的(de)发展中国家而言,Starlink提供(tígōng)的高速网络是(shì)唯一(wéiyī)可行的选择。Starlink凭借“先发优势(yōushì)”,自2019年起就开始大规模发射廉价小型卫星,并(bìng)在全球部署超过5000颗,服务范围涵盖60多个国家。马斯克的目标是最终将这一数字扩大到42000颗。这类低轨卫星群(LEO constellation)不仅(bùjǐn)覆盖密集,还具备更低通信延迟,是未来互联网基础架构的重要趋势。
由于地球轨道资源有限,其他公司难以再部署同等规模的网络,Starlink实质(shízhì)上通过技术“圈地”建立起(qǐ)事实上的垄断。轨道资源有限意味着(yìwèizhe)卫星不能无限部署,否则(fǒuzé)会造成碰撞(pèngzhuàng)风险和轨道拥堵,这让先到者占尽优势,后者无法进入。这种“数字公地的悲剧”意味着一项本应属全人类共享的资源,被一个私人资本集团封锁,并(bìng)反过来对全球市场进行长期控制。
研究者Ben Burgis近日在《雅各宾》的文章认为(rènwéi),将SpaceX和Starlink国有化(guóyǒuhuà)的时候到了。
他同意政策评论人马特·斯托勒(Matt Stoller)所指出的(de),从任何(rènhé)正常标准来看,SpaceX已是名副其实的“卫星发射垄断者”。更令人担忧(lìngréndānyōu)的是,SpaceX及其旗下的Starlink,其实是高度依赖政府资金发展的。虽然它是私人企业,但它的发展离不开 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měiguóguójiāhángkōnghángtiānjú))和美国国防部提供的巨额合同,其中很多甚至属于保密(bǎomì)项目。如果没有这些来自(láizì)纳税人的资金,SpaceX根本不可能达到今天的体量和地位。因此,说SpaceX是“自由市场创新”的典范,其实是一种误导——它是在(zài)(zài)国家扶持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却掌握在个人手中(shǒuzhōng)。
作者认为,虽然班农的出发点是临时性“接管(jiēguǎn)”,直到能找到所谓“稳定的管理团队”,但问题是,我们为何(wèihé)不将这样一个关键的战略基础设施长期纳入(nàrù)公共领域?
这是(zhèshì)一个重大的政策选择。反对国有化的人往往会说,私营企业效率更高、更有竞争力。但这些理由(lǐyóu)在SpaceX的案例(ànlì)中根本站不住脚——它根本没有处于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中,而是以压倒性优势占据了主导地位,已经(yǐjīng)被多次指控有垄断行为。
此外,SpaceX的(de)利润也不是由“市场机制”自然生成的,而是(érshì)建立在政府合同和补贴之上。换句话说,纳税人正在出钱(chūqián)资助一个(yígè)私人巨头,而这些收益却最终流入(liúrù)了埃隆·马斯克的个人财富,以及如Founders Fund和Draper Fisher Jurvetson等投资机构的资产组合中。
如果(rúguǒ)这些公共资金用于支持(zhīchí)一个由(yóu)政府直接运营的太空机构会怎么样?作者认为至少有两个好处:首先,资金不会再流向寡头个人财富。不必再让马斯克靠着国家支持进一步积累巨额个人资产。其次,太空政策可以真正接受民主监督。也就是说(yějiùshìshuō),像Starlink终端应该部署在哪里、哪些航天器是否退役等重大决定,将(jiāng)不再是某个个人的意愿,而是由政府机构作出,并对(duì)国会和公众负责。
这不仅能(néng)避免因为马斯克一时(yīshí)的态度转变而引发的地缘政治混乱,也能将太空探索真正纳入全民治理的轨道上。因此(yīncǐ)立即对SpaceX和Starlink实施国有化不仅必要,而且正当。
拥有选择(xuǎnzé)的(de)(de)权利就意味着拥有自由(zìyóu)(zìyóu)吗?选择等同于自由这一想法如何(rúhé)塑造了跨越全球的文化和政治?在今年2月由普林斯顿出版社出版的《选择时代:现代生活中的自由史(shǐ)》(The Age of Choice:A History of Freedom in Modern Life)一书中,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历史学家索菲亚·罗森菲尔德(Sophia Rosenfeld)以18世纪为起点,考察了选择这个错综复杂的概念的历史。罗森菲尔德穿梭在文学史(wénxuéshǐ)和政治史之间,追问(zhuīwèn)选择如何在我们对世界的思考中占据了如此中心的地位。
 《选择时代:现代生活中的(de)自由(zìyóu)史(shǐ)》(The Age of Choice:A History of Freedom in Modern Life)
尽管如今“选择”这一理念已无可争议地占据主导地位,但它(tā)长期以来(yǐlái)同时(tóngshí)受到来自左右两翼(liǎngyì)的(de)批评。自问世以来,《选择时代》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受到了很多(hěnduō)关注。在今年4月与《雅各宾》(Jacobin)杂志进行的题为“选择及其不满(Choice and Its Discontents)”的访谈中,罗森菲尔德对该书的主要观点及其在今日世界中的意义进行了介绍。
罗森菲尔德指出,这本书探讨了在(zài)美国以及现代世界的(de)大部分地区是(shì)如何逐渐将自由(zìyóu)视为从多个选项中做出选择(xuǎnzé)的能力的。我们逐渐将自由与选择珍爱的人、持有的思想、支持的政治平台或购买的产品(chǎnpǐn)联系起来。我们认为拥有和做出选择不仅是个人成就也是对我们作为自主个体的公共认可的来源。自由和选择并非永恒不变的理念,它们一直在演变,而她(tā)想要探究的主要问题是:这种自由的概念是如何发展的?它的利弊是什么?
自17世纪末以来,选择的概念逐渐发展,涉及消费品、思想、宗教价值观、伴侣、性取向和(hé)政治(zhèngzhì)。其中,政治选择是一项晚近的发展,迟至十九世纪末才开始出现(chūxiàn),彼时人们开始将政治想象为一系列私下的、个人的决策,并将秘密投票视为其最佳实践(shíjiàn)途径。二十世纪巩固(gǒnggù)了这种文化转变,广告学、心理学、精神病学和经济学(jīngjìxué)等新兴(xīnxīng)领域开始研究人们如何以及为何(wèihé)做出选择。这些领域将“人是选择者”这一理念自然化,并将其构建为普遍真理。这种根植于社会科学和政治学的个人自主性理念如今定义了我们对自我(zìwǒ)的理解。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始终将生活视为一系列基于个人偏好的个体选择。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下(dāngxià),都有许多人反对这种观念。
《选择时代》的书封上印着(zhe)一名(yīmíng)女顾客在自动售货机前购物的照片。罗森菲尔德在访谈中说,自动售货机象征着二战后的选择文化,它是(shì)人(rén)们关于选择的记忆中的一个高峰,很多人至今对其充满怀旧之情。自动售货机标志着自助服务(fúwù)模式的开端,和现代超市一样走向了全球。而今天的网上购物尽管仍然是自助服务的延续,但它缺乏真实市场的实感,过多的选择可能会让人感到沮丧或不知所措,已经(yǐjīng)演变成一种截然不同的体验。与此同时,自动售货机也代表(dàibiǎo)着一个悖论,它既是自由的象征,也标志着一种至今依然存在的、更为狭隘的选择观。
罗森(luósēn)菲尔德谈到,在19世纪,女性及其男性盟友一度(yídù)将(jiāng)选择(xuǎnzé)(xuǎnzé)视为一种赋权的方式,他们相信当女性能够在家庭生活领域做出选择,她们就能在政治或其他领域做出选择。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新(xīn)自由主义的兴起,这种观念达到了顶峰,尤其是在罗诉韦德案在美国使堕胎合法化之后,女权主义者认为选择权是一个不仅能够使堕胎变得合法,同时(tóngshí)也可以令其被社会接受的解决方案,因为它允许每个女性自行决定什么是对自己最有利的,而无需强迫(qiǎngpò)其他人认同这一选择。将个人选择权提升为一项基本权利也与(yǔ)资本主义和民主价值观相契合。
但是,女性很快发现选择(xuǎnzé)也造成了不平等。“选择权(right to choose)”受到了来自左右两翼的挑战:右翼以“生命权(right to life)”进行反驳,认为选择理念道德浅薄;左翼的批评则集中在选择的物质现实(xiànshí)上:当人们缺乏行动的手段(shǒuduàn)时,给予他们选择权有何意义?如果一个人负担不起某个选择,抑或没有时间(shíjiān)或支持使某个选项变得切实可行,这真的算是一种选择吗?这种批评,尤其是来自黑人女权主义者(nǚquánzhǔyìzhě)的批评,凸显了选择在实践中的局限性,并且同样可以延伸到人权和(hé)商业领域。例如择校的自由看似是给予主动权(zhǔdòngquán),但它带来(dàilái)的自由比不上建立一个有效(yǒuxiào)的公共学校(xuéxiào)系统,即使后者意味着对个人选择的限制。人们还经常(jīngcháng)因为做出“坏”选择而受到指责(zhǐzé),即使他们缺乏做出更好选择的结构性支持时也是如此,选择由此加剧了不平等。
罗森(luósēn)菲尔德还提到,本书的(de)(de)(de)写作始于特朗普第一任期之前,也即奥巴马执政后期,当时她相信政治轨迹会延续下去,但情况显然发生了变化(biànhuà)。特朗普执政的最初几年间(jiān),罗森菲尔德暂停了关于本书的工作,转而写作探讨特朗普任期内愈加明显的政治两极分化和围绕真相的冲突的《民主(mínzhǔ)与真相:一部短历史》(Democracy and Truth: A Short History)一书(yīshū)。当她重新(xīn)回到《选择时代》时,在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的政治转变的影响下,她的视角发生了变化。从生殖选择到择校,两届政府对“选择”这一概念进行了不同的运用,反映了政治话语的更(gèng)广泛变化。罗森菲尔德表示,尽管她仍在思考新特朗普时代与本书论点的具体(jùtǐ)关联,但这本书对当前的政治动态的确有所洞察。
她特别指出,美国并非第一个尝试与资本主义经济紧密相连(xiānglián)的威权民主的国家(guójiā)。有贝卢斯科尼、欧尔班和(hé)博索纳罗等领导人作为先例,特朗普已将基于选择(xuǎnzé)的语言融入其政策(zhèngcè),尤其是在(zài)消费品和教育领域。但这种“选择自由”的论调主要在消费领域运作,在强调个人自主权的同时巩固国家权力。在这种新的政治(zhèngzhì)环境下,选择发生了突变。美国迎来的是消费领域的自由主义与政治领域的威权主义的混合,前者鼓励企业和个人做出选择,后者则要求由国家控制所有可用选项。
针对(zhēnduì)《选择(xuǎnzé)时代》是否应该被理解为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批判这一问题,罗森菲尔德表示(biǎoshì),本书并非反资本主义的战书,它更侧重于(cèzhòngyú)鼓励人们进行自我(zìwǒ)反思:经由选择对自由进行概念化如何同时带来了解放和束缚。虽然选择本身就(jiù)具有解放性(xìng)——这在废奴主义和女权主义等运动中至关重要——但它并不总是赋予人们自主权。她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和民主及人权理想是选择理念产生的两个源头,随着(suízhe)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二战之后,这两个源头趋于融合,但今天人们可能会见证这一融合的瓦解,尽管这不太可能不受抵抗地发生。
罗森菲尔德最后总结道,在一个充满了不平等的机会有限的世界中,我们必须(bìxū)谨慎地不把选择作为一个简单(jiǎndān)的解决方案。
密歇根大学的(de)现代科学与(yǔ)医学史专家亨利·M·考尔斯(Henry M. Cowles)在(zài)今年2月为《洛杉矶书评》撰写的题为“发牌(fāpái)者的选择(xuǎnzé)(xuǎnzé):自由是什么以及不是(búshì)什么(Dealer's Choice: What Freedom Is—and Isn't)”的评论文章中,对《选择时代》大加赞扬。他说自己在读完(dúwán)此书之后,几乎每次做出选择时都会想到书中的某个论点或案例,进而(jìnér)反思“是我做的选择吗?(如果不是,那么)是谁做的?为什么这么选?”。考尔斯写到,如果你觉得自由应该意味着比(有限)选择更多的东西(dōngxī),或者甚至是你只是想知道菜单是谁制作的、哪些选项没有被写上去(xiěshǎngqù),那么你就会和罗森菲尔德一样,怀疑当自由被等同于选择,我们得到的和失去的一样多。
《选择时代》让考尔斯深信,我们(wǒmen)被选择所包围,但我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做出选择。正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著名的(de)(de)论断——我们是“习惯的集合体(jíhétǐ)”——所说的那样,我们对被给予的做出反应,适应我们找到的,吃我们喜欢(xǐhuān)的——同时试图说服自己,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自由的。自由和选择远非同义词,它们(tāmen)更像是反义词,或者至少是两个彼此之间存在着令人不安的张力的词汇。他(tā)套用(tàoyòng)了科技(kējì)史学家常说的那句话:选择既无好坏之分,也(yě)非中立。一切都取决于选项是什么,取决于选择在强制和自由之间的光谱上处于哪个位置,取决于人们是否可以拒绝选择,或者选择一些从来没有人想到过的东西。
《纽约书评》近日刊登了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de)美国历史学家(lìshǐxuéjiā)戴维·A·贝尔(David A. Bell)为《选择(xuǎnzé)时代》撰写的书评“我的自由,我的选择(My Freedom,My Choice)”。贝尔同(tóng)样赞扬了罗森菲尔德此书的原创性,认为(rènwéi)《选择时代》通过揭示新旧两种自由观之间的差异,讲述(jiǎngshù)了一个长期被隐藏的重要故事。新自由观将个人拥有选择和做出选择与(yǔ)自由相等同,旧自由观则认为重要的是个人做出选择时的道德目的,而非选择这一行为本身(běnshēn)。贝尔指出,此前大多数自由史著作大多集中在高层政治和经典政治理论领域(lǐngyù),此书则超越(chāoyuè)了这一领域,迫使我们从新的视角思考自由的历史和本质。
不过,贝尔(bèiěr)的(de)(de)评论中并不全是溢美之词,他指出了这部著作的两点(liǎngdiǎn)瑕疵。首先,贝尔认为,罗森菲尔德在结论中说(shuō)“选择从自由(zìyóu)的一项福利变成了自由的本质”,以及她反复强调在现代选择被视为(shìwèi)“基本上价值中立”,即使在“国家政治(zhèngzhì)生活”中也是如此,这些说法有些言过其实。贝尔认为,在属于现代的战争和革命期间(qījiān),例如在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演讲中,对(duì)自由的捍卫仍要更接近将自由视为能够不受束缚地为共同利益而行动的旧自由观。从某种意义上说,罗森菲尔德讲述的是个人经历和私人生活——与群体经历和公共生活相对——如何日益被视为政治价值观的主要来源,但(dàn)个人到政治的转变从未彻底完成。在某些情况下,选择或许看起来像是“自由的本质”,但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如此。
其次,在(zài)贝尔看来,罗森菲尔德的根本观点是,问题最终关乎道德(dàodé),并且“选择本身需要……更(gèng)明确地与(yǔ)基本的道德考量联系起来”,然而在我们的社会中,对于(duìyú)这些“基本道德考量”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几乎没有达成共识,而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一个糟糕的决策(juécè)工具。在我们这个世俗且精神支离破碎的时代,正是因为引发分歧的道德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才使得我们默认退回到(dào)“基本价值(jiàzhí)中立”的选择理想,这也许是解决道德问题的最糟糕的方式,但可能已经要比其他所有方式都更无害。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xiàzài)“澎湃新闻”APP)
《选择时代:现代生活中的(de)自由(zìyóu)史(shǐ)》(The Age of Choice:A History of Freedom in Modern Life)
尽管如今“选择”这一理念已无可争议地占据主导地位,但它(tā)长期以来(yǐlái)同时(tóngshí)受到来自左右两翼(liǎngyì)的(de)批评。自问世以来,《选择时代》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受到了很多(hěnduō)关注。在今年4月与《雅各宾》(Jacobin)杂志进行的题为“选择及其不满(Choice and Its Discontents)”的访谈中,罗森菲尔德对该书的主要观点及其在今日世界中的意义进行了介绍。
罗森菲尔德指出,这本书探讨了在(zài)美国以及现代世界的(de)大部分地区是(shì)如何逐渐将自由(zìyóu)视为从多个选项中做出选择(xuǎnzé)的能力的。我们逐渐将自由与选择珍爱的人、持有的思想、支持的政治平台或购买的产品(chǎnpǐn)联系起来。我们认为拥有和做出选择不仅是个人成就也是对我们作为自主个体的公共认可的来源。自由和选择并非永恒不变的理念,它们一直在演变,而她(tā)想要探究的主要问题是:这种自由的概念是如何发展的?它的利弊是什么?
自17世纪末以来,选择的概念逐渐发展,涉及消费品、思想、宗教价值观、伴侣、性取向和(hé)政治(zhèngzhì)。其中,政治选择是一项晚近的发展,迟至十九世纪末才开始出现(chūxiàn),彼时人们开始将政治想象为一系列私下的、个人的决策,并将秘密投票视为其最佳实践(shíjiàn)途径。二十世纪巩固(gǒnggù)了这种文化转变,广告学、心理学、精神病学和经济学(jīngjìxué)等新兴(xīnxīng)领域开始研究人们如何以及为何(wèihé)做出选择。这些领域将“人是选择者”这一理念自然化,并将其构建为普遍真理。这种根植于社会科学和政治学的个人自主性理念如今定义了我们对自我(zìwǒ)的理解。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始终将生活视为一系列基于个人偏好的个体选择。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下(dāngxià),都有许多人反对这种观念。
《选择时代》的书封上印着(zhe)一名(yīmíng)女顾客在自动售货机前购物的照片。罗森菲尔德在访谈中说,自动售货机象征着二战后的选择文化,它是(shì)人(rén)们关于选择的记忆中的一个高峰,很多人至今对其充满怀旧之情。自动售货机标志着自助服务(fúwù)模式的开端,和现代超市一样走向了全球。而今天的网上购物尽管仍然是自助服务的延续,但它缺乏真实市场的实感,过多的选择可能会让人感到沮丧或不知所措,已经(yǐjīng)演变成一种截然不同的体验。与此同时,自动售货机也代表(dàibiǎo)着一个悖论,它既是自由的象征,也标志着一种至今依然存在的、更为狭隘的选择观。
罗森(luósēn)菲尔德谈到,在19世纪,女性及其男性盟友一度(yídù)将(jiāng)选择(xuǎnzé)(xuǎnzé)视为一种赋权的方式,他们相信当女性能够在家庭生活领域做出选择,她们就能在政治或其他领域做出选择。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新(xīn)自由主义的兴起,这种观念达到了顶峰,尤其是在罗诉韦德案在美国使堕胎合法化之后,女权主义者认为选择权是一个不仅能够使堕胎变得合法,同时(tóngshí)也可以令其被社会接受的解决方案,因为它允许每个女性自行决定什么是对自己最有利的,而无需强迫(qiǎngpò)其他人认同这一选择。将个人选择权提升为一项基本权利也与(yǔ)资本主义和民主价值观相契合。
但是,女性很快发现选择(xuǎnzé)也造成了不平等。“选择权(right to choose)”受到了来自左右两翼的挑战:右翼以“生命权(right to life)”进行反驳,认为选择理念道德浅薄;左翼的批评则集中在选择的物质现实(xiànshí)上:当人们缺乏行动的手段(shǒuduàn)时,给予他们选择权有何意义?如果一个人负担不起某个选择,抑或没有时间(shíjiān)或支持使某个选项变得切实可行,这真的算是一种选择吗?这种批评,尤其是来自黑人女权主义者(nǚquánzhǔyìzhě)的批评,凸显了选择在实践中的局限性,并且同样可以延伸到人权和(hé)商业领域。例如择校的自由看似是给予主动权(zhǔdòngquán),但它带来(dàilái)的自由比不上建立一个有效(yǒuxiào)的公共学校(xuéxiào)系统,即使后者意味着对个人选择的限制。人们还经常(jīngcháng)因为做出“坏”选择而受到指责(zhǐzé),即使他们缺乏做出更好选择的结构性支持时也是如此,选择由此加剧了不平等。
罗森(luósēn)菲尔德还提到,本书的(de)(de)(de)写作始于特朗普第一任期之前,也即奥巴马执政后期,当时她相信政治轨迹会延续下去,但情况显然发生了变化(biànhuà)。特朗普执政的最初几年间(jiān),罗森菲尔德暂停了关于本书的工作,转而写作探讨特朗普任期内愈加明显的政治两极分化和围绕真相的冲突的《民主(mínzhǔ)与真相:一部短历史》(Democracy and Truth: A Short History)一书(yīshū)。当她重新(xīn)回到《选择时代》时,在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的政治转变的影响下,她的视角发生了变化。从生殖选择到择校,两届政府对“选择”这一概念进行了不同的运用,反映了政治话语的更(gèng)广泛变化。罗森菲尔德表示,尽管她仍在思考新特朗普时代与本书论点的具体(jùtǐ)关联,但这本书对当前的政治动态的确有所洞察。
她特别指出,美国并非第一个尝试与资本主义经济紧密相连(xiānglián)的威权民主的国家(guójiā)。有贝卢斯科尼、欧尔班和(hé)博索纳罗等领导人作为先例,特朗普已将基于选择(xuǎnzé)的语言融入其政策(zhèngcè),尤其是在(zài)消费品和教育领域。但这种“选择自由”的论调主要在消费领域运作,在强调个人自主权的同时巩固国家权力。在这种新的政治(zhèngzhì)环境下,选择发生了突变。美国迎来的是消费领域的自由主义与政治领域的威权主义的混合,前者鼓励企业和个人做出选择,后者则要求由国家控制所有可用选项。
针对(zhēnduì)《选择(xuǎnzé)时代》是否应该被理解为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批判这一问题,罗森菲尔德表示(biǎoshì),本书并非反资本主义的战书,它更侧重于(cèzhòngyú)鼓励人们进行自我(zìwǒ)反思:经由选择对自由进行概念化如何同时带来了解放和束缚。虽然选择本身就(jiù)具有解放性(xìng)——这在废奴主义和女权主义等运动中至关重要——但它并不总是赋予人们自主权。她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和民主及人权理想是选择理念产生的两个源头,随着(suízhe)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二战之后,这两个源头趋于融合,但今天人们可能会见证这一融合的瓦解,尽管这不太可能不受抵抗地发生。
罗森菲尔德最后总结道,在一个充满了不平等的机会有限的世界中,我们必须(bìxū)谨慎地不把选择作为一个简单(jiǎndān)的解决方案。
密歇根大学的(de)现代科学与(yǔ)医学史专家亨利·M·考尔斯(Henry M. Cowles)在(zài)今年2月为《洛杉矶书评》撰写的题为“发牌(fāpái)者的选择(xuǎnzé)(xuǎnzé):自由是什么以及不是(búshì)什么(Dealer's Choice: What Freedom Is—and Isn't)”的评论文章中,对《选择时代》大加赞扬。他说自己在读完(dúwán)此书之后,几乎每次做出选择时都会想到书中的某个论点或案例,进而(jìnér)反思“是我做的选择吗?(如果不是,那么)是谁做的?为什么这么选?”。考尔斯写到,如果你觉得自由应该意味着比(有限)选择更多的东西(dōngxī),或者甚至是你只是想知道菜单是谁制作的、哪些选项没有被写上去(xiěshǎngqù),那么你就会和罗森菲尔德一样,怀疑当自由被等同于选择,我们得到的和失去的一样多。
《选择时代》让考尔斯深信,我们(wǒmen)被选择所包围,但我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做出选择。正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著名的(de)(de)论断——我们是“习惯的集合体(jíhétǐ)”——所说的那样,我们对被给予的做出反应,适应我们找到的,吃我们喜欢(xǐhuān)的——同时试图说服自己,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自由的。自由和选择远非同义词,它们(tāmen)更像是反义词,或者至少是两个彼此之间存在着令人不安的张力的词汇。他(tā)套用(tàoyòng)了科技(kējì)史学家常说的那句话:选择既无好坏之分,也(yě)非中立。一切都取决于选项是什么,取决于选择在强制和自由之间的光谱上处于哪个位置,取决于人们是否可以拒绝选择,或者选择一些从来没有人想到过的东西。
《纽约书评》近日刊登了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de)美国历史学家(lìshǐxuéjiā)戴维·A·贝尔(David A. Bell)为《选择(xuǎnzé)时代》撰写的书评“我的自由,我的选择(My Freedom,My Choice)”。贝尔同(tóng)样赞扬了罗森菲尔德此书的原创性,认为(rènwéi)《选择时代》通过揭示新旧两种自由观之间的差异,讲述(jiǎngshù)了一个长期被隐藏的重要故事。新自由观将个人拥有选择和做出选择与(yǔ)自由相等同,旧自由观则认为重要的是个人做出选择时的道德目的,而非选择这一行为本身(běnshēn)。贝尔指出,此前大多数自由史著作大多集中在高层政治和经典政治理论领域(lǐngyù),此书则超越(chāoyuè)了这一领域,迫使我们从新的视角思考自由的历史和本质。
不过,贝尔(bèiěr)的(de)(de)评论中并不全是溢美之词,他指出了这部著作的两点(liǎngdiǎn)瑕疵。首先,贝尔认为,罗森菲尔德在结论中说(shuō)“选择从自由(zìyóu)的一项福利变成了自由的本质”,以及她反复强调在现代选择被视为(shìwèi)“基本上价值中立”,即使在“国家政治(zhèngzhì)生活”中也是如此,这些说法有些言过其实。贝尔认为,在属于现代的战争和革命期间(qījiān),例如在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演讲中,对(duì)自由的捍卫仍要更接近将自由视为能够不受束缚地为共同利益而行动的旧自由观。从某种意义上说,罗森菲尔德讲述的是个人经历和私人生活——与群体经历和公共生活相对——如何日益被视为政治价值观的主要来源,但(dàn)个人到政治的转变从未彻底完成。在某些情况下,选择或许看起来像是“自由的本质”,但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如此。
其次,在(zài)贝尔看来,罗森菲尔德的根本观点是,问题最终关乎道德(dàodé),并且“选择本身需要……更(gèng)明确地与(yǔ)基本的道德考量联系起来”,然而在我们的社会中,对于(duìyú)这些“基本道德考量”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几乎没有达成共识,而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一个糟糕的决策(juécè)工具。在我们这个世俗且精神支离破碎的时代,正是因为引发分歧的道德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才使得我们默认退回到(dào)“基本价值(jiàzhí)中立”的选择理想,这也许是解决道德问题的最糟糕的方式,但可能已经要比其他所有方式都更无害。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xiàzài)“澎湃新闻”APP)
 当地时间(shíjiān)2025年6月7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SpaceX公司(gōngsī)猎鹰9号火箭于凌晨0时54分发射升空。
Starlink是(shì)SpaceX的全球卫星互联网服务,目前占据全球约三分之二的卫星总量(zǒngliàng)。用户只需一根小型接收天线,就(jiù)可以(kěyǐ)在世界任何地方接入高速网络。在俄乌(wū)战争中,马斯克可以决定是否允许乌军使用Starlink来作战——这给了他类似主权国家的权力。
最近,特朗普威胁要切断马斯克的政府合同资金(特别是SpaceX),作为政治报复。而马斯克也不甘示弱,暗示(ànshì)如果(rúguǒ)遭到(zāodào)打击,他(tā)可能会停止某些关键服务,比如“关闭龙飞船”或干扰美国军事通信。
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是特朗普的(de)前首席战略顾问,现在(xiànzài)又(yòu)回到其身边。他提出一个大胆建议:政府应该动用《国防生产法》,将SpaceX收归国有。《国防生产法》(Defense Production Act)是一部(yībù)1950年在朝鲜战争背景下(xià)颁布的联邦法律,允许(yǔnxǔ)美国总统在国家(guójiā)紧急情况下优先调配工业资源,以支持国防与国家安全目标。这部法律在新冠疫情期间也曾被(bèi)特朗普用来强制企业生产呼吸机和个人防护装备。班农的意思是:SpaceX已经成为类似“电网”或“军队通信”的基础设施,不能只(zhǐ)由一个人控制。“基础设施”在这里不仅仅指(zhǐ)物理层面,也包括信息和战略意义上的“平台控制力”,即一个企业对社会运行的关键路径拥有(yōngyǒu)决定权。
虽然SpaceX的技术确实有优势(火箭可重复使用、发射(fāshè)成本低),但它(tā)也被业界指责为通过不公平竞争打压对手(duìshǒu)。以下是《纽约时报》曾报道的几起例子:
新一代的太空创业者们(men)试图(shìtú)模仿(mófǎng)马斯克,但他们对马斯克被认为采用的反竞争手段(指通过不公平的方式限制竞争对手,保护自己市场地位的行为)感到担忧。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公开挑战他。
蒂姆(dìmǔ)·埃利斯(Tim Ellis)受到了马斯克想造出能载人去火星的(de)火箭的激励,创办了Relativity Space(一个火箭制造公司)。后来他(tā)听说,有些与SpaceX有关联的人在试图阻止他为自己的火星项目筹钱(chóuqián)。
吉姆·坎特雷尔(léiěr)(Jim Cantrell)是2002年(nián)和马斯克一起创办SpaceX的(de)。后来他创立了自己的火箭发射公司Phantom Space。可是,两位潜在(qiánzài)客户告诉他的销售(xiāoshòu)团队,因为SpaceX在合同中加入了限制条款(合同条款中写明不允许客户同时使用竞争对手的服务),他们无法和他签约。
彼得·贝克(Peter Beck)是新西兰的(de)航天工程师,2019年曾和马斯克见面,谈他的公司Rocket Lab。几个月后,SpaceX开始以优惠价运送小型货物(小型货物指(zhǐ)体积或重量较小的货物),贝克和其他(qítā)业内人士认为这是(zhèshì)为了压制竞争对手、降低他们的成功机会(jīhuì)。
这些(zhèxiē)行为(xíngwéi)包括:低于成本发射,以极低价格让对手无法生存(shēngcún);“优先拒绝权(quán)”条款:客户若找到更便宜的(de)竞争者,SpaceX有权“抢单”;偏袒自己公司(如Starlink):同样是发射卫星,Starlink获得更便宜报价;干扰竞争对手融资;进入门槛高(需要巨额资本与许可)。这些都是典型的垄断行为。
之前学者Siva Vaidhyanathan在《The Nation》杂志(zázhì)上的(de)评论文章就认为,马斯克之所以成为21世纪最具(zuìjù)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制造了电动汽车或(huò)发射了火箭,而是因为他掌握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的力量形式——对全球互联网(hùliánwǎng)连接的控制权,特别是通过卫星互联网。他能够随意地打开(dǎkāi)或关闭数百万人的网络接入,就像扳动水龙头一样。
虽然SpaceX是私人公司,但它从公共资金中获得了大量支持(zhīchí)。Starlink的意义,在(zài)(zài)俄乌冲突爆发后变得极为突出(tūchū)。自2022年2月战争爆发以来,Starlink为乌克兰的平民和军队提供了关键的通信服务。马斯克最初同意在乌克兰上空部署大量Starlink卫星,费用由(yóu)他承担(chéngdān),而接收终端设备则由北约国家和私人捐助者提供。
但问题随即出现。马斯克(mǎsīkè)拒绝将Starlink信号延伸至被俄罗斯(éluósī)占领的乌克兰地区(dìqū)(例如克里米亚(kèlǐmǐyà)和顿巴斯),理由是他不想“卷入战争升级或制造重大军事冲突”。这种做法实际上默认了俄罗斯对这些地区的非法主张,完全无视乌克兰的主权、国际法和人权问题。
这就是一个危险的(de)信号:战争冲突中(zhōng)最基本的通信手段,竟然落入了一个私人(sīrén)企业家的手中。他不是依据国际准则或多边协议行事,而是凭借个人意志和判断,左右一个主权国家的信息生命线。
当地时间(shíjiān)2025年6月7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SpaceX公司(gōngsī)猎鹰9号火箭于凌晨0时54分发射升空。
Starlink是(shì)SpaceX的全球卫星互联网服务,目前占据全球约三分之二的卫星总量(zǒngliàng)。用户只需一根小型接收天线,就(jiù)可以(kěyǐ)在世界任何地方接入高速网络。在俄乌(wū)战争中,马斯克可以决定是否允许乌军使用Starlink来作战——这给了他类似主权国家的权力。
最近,特朗普威胁要切断马斯克的政府合同资金(特别是SpaceX),作为政治报复。而马斯克也不甘示弱,暗示(ànshì)如果(rúguǒ)遭到(zāodào)打击,他(tā)可能会停止某些关键服务,比如“关闭龙飞船”或干扰美国军事通信。
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是特朗普的(de)前首席战略顾问,现在(xiànzài)又(yòu)回到其身边。他提出一个大胆建议:政府应该动用《国防生产法》,将SpaceX收归国有。《国防生产法》(Defense Production Act)是一部(yībù)1950年在朝鲜战争背景下(xià)颁布的联邦法律,允许(yǔnxǔ)美国总统在国家(guójiā)紧急情况下优先调配工业资源,以支持国防与国家安全目标。这部法律在新冠疫情期间也曾被(bèi)特朗普用来强制企业生产呼吸机和个人防护装备。班农的意思是:SpaceX已经成为类似“电网”或“军队通信”的基础设施,不能只(zhǐ)由一个人控制。“基础设施”在这里不仅仅指(zhǐ)物理层面,也包括信息和战略意义上的“平台控制力”,即一个企业对社会运行的关键路径拥有(yōngyǒu)决定权。
虽然SpaceX的技术确实有优势(火箭可重复使用、发射(fāshè)成本低),但它(tā)也被业界指责为通过不公平竞争打压对手(duìshǒu)。以下是《纽约时报》曾报道的几起例子:
新一代的太空创业者们(men)试图(shìtú)模仿(mófǎng)马斯克,但他们对马斯克被认为采用的反竞争手段(指通过不公平的方式限制竞争对手,保护自己市场地位的行为)感到担忧。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公开挑战他。
蒂姆(dìmǔ)·埃利斯(Tim Ellis)受到了马斯克想造出能载人去火星的(de)火箭的激励,创办了Relativity Space(一个火箭制造公司)。后来他(tā)听说,有些与SpaceX有关联的人在试图阻止他为自己的火星项目筹钱(chóuqián)。
吉姆·坎特雷尔(léiěr)(Jim Cantrell)是2002年(nián)和马斯克一起创办SpaceX的(de)。后来他创立了自己的火箭发射公司Phantom Space。可是,两位潜在(qiánzài)客户告诉他的销售(xiāoshòu)团队,因为SpaceX在合同中加入了限制条款(合同条款中写明不允许客户同时使用竞争对手的服务),他们无法和他签约。
彼得·贝克(Peter Beck)是新西兰的(de)航天工程师,2019年曾和马斯克见面,谈他的公司Rocket Lab。几个月后,SpaceX开始以优惠价运送小型货物(小型货物指(zhǐ)体积或重量较小的货物),贝克和其他(qítā)业内人士认为这是(zhèshì)为了压制竞争对手、降低他们的成功机会(jīhuì)。
这些(zhèxiē)行为(xíngwéi)包括:低于成本发射,以极低价格让对手无法生存(shēngcún);“优先拒绝权(quán)”条款:客户若找到更便宜的(de)竞争者,SpaceX有权“抢单”;偏袒自己公司(如Starlink):同样是发射卫星,Starlink获得更便宜报价;干扰竞争对手融资;进入门槛高(需要巨额资本与许可)。这些都是典型的垄断行为。
之前学者Siva Vaidhyanathan在《The Nation》杂志(zázhì)上的(de)评论文章就认为,马斯克之所以成为21世纪最具(zuìjù)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制造了电动汽车或(huò)发射了火箭,而是因为他掌握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的力量形式——对全球互联网(hùliánwǎng)连接的控制权,特别是通过卫星互联网。他能够随意地打开(dǎkāi)或关闭数百万人的网络接入,就像扳动水龙头一样。
虽然SpaceX是私人公司,但它从公共资金中获得了大量支持(zhīchí)。Starlink的意义,在(zài)(zài)俄乌冲突爆发后变得极为突出(tūchū)。自2022年2月战争爆发以来,Starlink为乌克兰的平民和军队提供了关键的通信服务。马斯克最初同意在乌克兰上空部署大量Starlink卫星,费用由(yóu)他承担(chéngdān),而接收终端设备则由北约国家和私人捐助者提供。
但问题随即出现。马斯克(mǎsīkè)拒绝将Starlink信号延伸至被俄罗斯(éluósī)占领的乌克兰地区(dìqū)(例如克里米亚(kèlǐmǐyà)和顿巴斯),理由是他不想“卷入战争升级或制造重大军事冲突”。这种做法实际上默认了俄罗斯对这些地区的非法主张,完全无视乌克兰的主权、国际法和人权问题。
这就是一个危险的(de)信号:战争冲突中(zhōng)最基本的通信手段,竟然落入了一个私人(sīrén)企业家的手中。他不是依据国际准则或多边协议行事,而是凭借个人意志和判断,左右一个主权国家的信息生命线。
 当地时间2025年(nián)2月(yuè)11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特斯拉和SpaceX首席执行官伊隆·马斯克在白宫椭圆形(tuǒyuánxíng)办公室,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活动。
马斯克拥有的(de),不(bù)仅是商业成功,更是一种足以改变战争(zhànzhēng)进程的、从未有人掌握过的通讯(tōngxùn)控制权。过去的媒体大亨,如(rú)赫斯特(20世纪初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报业大亨,拥有多家报纸和媒体,他通过夸大和煽动新闻,特别是在美西战争期间,制造公众对西班牙的敌意,推动美国政府对西班牙宣战(xuānzhàn),他被认为是Yellow journalism的代表人物,利用媒体操纵舆论,激发民族主义和战争情绪,从而影响国家政策和战争走向),可以操纵舆论推动战争;金融巨头如J.P.摩根,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zhōng)资助参战国。但他们并(bìng)不具备像马斯克这样,直接通过技术(jìshù)平台“关闭战场Wi-Fi”的能力。
Starlink的“地理围栏(wéilán)限制”(geofence)丑闻反映了一个(yígè)严峻现实:马斯克可以凭一己喜好,决定一个国家的军队是否还(hái)(hái)能指挥作战,一个企业是否还能运作,一个媒体是否还能报道。他的情绪和立场,可能成为左右国家命运的变量。
乌克兰并(bìng)不是唯一被Starlink影响的(de)地区。事实上,马斯克正低调地推动一个更宏大的图景(tújǐng)——重塑全球数字通信系统,使之以他个人意志为核心。如今世界各国试图摆脱Meta(Facebook母公司(mǔgōngsī))、Alphabet(谷歌母公司)等美国巨头的控制,以实现“数字主权”。但在(zài)这一过程中,它们(tāmen)却在网络基础设施层面被Starlink套牢。
对于许多基础薄弱、地广人稀的(de)发展中国家而言,Starlink提供(tígōng)的高速网络是(shì)唯一(wéiyī)可行的选择。Starlink凭借“先发优势(yōushì)”,自2019年起就开始大规模发射廉价小型卫星,并(bìng)在全球部署超过5000颗,服务范围涵盖60多个国家。马斯克的目标是最终将这一数字扩大到42000颗。这类低轨卫星群(LEO constellation)不仅(bùjǐn)覆盖密集,还具备更低通信延迟,是未来互联网基础架构的重要趋势。
由于地球轨道资源有限,其他公司难以再部署同等规模的网络,Starlink实质(shízhì)上通过技术“圈地”建立起(qǐ)事实上的垄断。轨道资源有限意味着(yìwèizhe)卫星不能无限部署,否则(fǒuzé)会造成碰撞(pèngzhuàng)风险和轨道拥堵,这让先到者占尽优势,后者无法进入。这种“数字公地的悲剧”意味着一项本应属全人类共享的资源,被一个私人资本集团封锁,并(bìng)反过来对全球市场进行长期控制。
研究者Ben Burgis近日在《雅各宾》的文章认为(rènwéi),将SpaceX和Starlink国有化(guóyǒuhuà)的时候到了。
他同意政策评论人马特·斯托勒(Matt Stoller)所指出的(de),从任何(rènhé)正常标准来看,SpaceX已是名副其实的“卫星发射垄断者”。更令人担忧(lìngréndānyōu)的是,SpaceX及其旗下的Starlink,其实是高度依赖政府资金发展的。虽然它是私人企业,但它的发展离不开 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měiguóguójiāhángkōnghángtiānjú))和美国国防部提供的巨额合同,其中很多甚至属于保密(bǎomì)项目。如果没有这些来自(láizì)纳税人的资金,SpaceX根本不可能达到今天的体量和地位。因此,说SpaceX是“自由市场创新”的典范,其实是一种误导——它是在(zài)(zài)国家扶持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却掌握在个人手中(shǒuzhōng)。
作者认为,虽然班农的出发点是临时性“接管(jiēguǎn)”,直到能找到所谓“稳定的管理团队”,但问题是,我们为何(wèihé)不将这样一个关键的战略基础设施长期纳入(nàrù)公共领域?
这是(zhèshì)一个重大的政策选择。反对国有化的人往往会说,私营企业效率更高、更有竞争力。但这些理由(lǐyóu)在SpaceX的案例(ànlì)中根本站不住脚——它根本没有处于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中,而是以压倒性优势占据了主导地位,已经(yǐjīng)被多次指控有垄断行为。
此外,SpaceX的(de)利润也不是由“市场机制”自然生成的,而是(érshì)建立在政府合同和补贴之上。换句话说,纳税人正在出钱(chūqián)资助一个(yígè)私人巨头,而这些收益却最终流入(liúrù)了埃隆·马斯克的个人财富,以及如Founders Fund和Draper Fisher Jurvetson等投资机构的资产组合中。
如果(rúguǒ)这些公共资金用于支持(zhīchí)一个由(yóu)政府直接运营的太空机构会怎么样?作者认为至少有两个好处:首先,资金不会再流向寡头个人财富。不必再让马斯克靠着国家支持进一步积累巨额个人资产。其次,太空政策可以真正接受民主监督。也就是说(yějiùshìshuō),像Starlink终端应该部署在哪里、哪些航天器是否退役等重大决定,将(jiāng)不再是某个个人的意愿,而是由政府机构作出,并对(duì)国会和公众负责。
这不仅能(néng)避免因为马斯克一时(yīshí)的态度转变而引发的地缘政治混乱,也能将太空探索真正纳入全民治理的轨道上。因此(yīncǐ)立即对SpaceX和Starlink实施国有化不仅必要,而且正当。
拥有选择(xuǎnzé)的(de)(de)权利就意味着拥有自由(zìyóu)(zìyóu)吗?选择等同于自由这一想法如何(rúhé)塑造了跨越全球的文化和政治?在今年2月由普林斯顿出版社出版的《选择时代:现代生活中的自由史(shǐ)》(The Age of Choice:A History of Freedom in Modern Life)一书中,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历史学家索菲亚·罗森菲尔德(Sophia Rosenfeld)以18世纪为起点,考察了选择这个错综复杂的概念的历史。罗森菲尔德穿梭在文学史(wénxuéshǐ)和政治史之间,追问(zhuīwèn)选择如何在我们对世界的思考中占据了如此中心的地位。
当地时间2025年(nián)2月(yuè)11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特斯拉和SpaceX首席执行官伊隆·马斯克在白宫椭圆形(tuǒyuánxíng)办公室,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活动。
马斯克拥有的(de),不(bù)仅是商业成功,更是一种足以改变战争(zhànzhēng)进程的、从未有人掌握过的通讯(tōngxùn)控制权。过去的媒体大亨,如(rú)赫斯特(20世纪初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报业大亨,拥有多家报纸和媒体,他通过夸大和煽动新闻,特别是在美西战争期间,制造公众对西班牙的敌意,推动美国政府对西班牙宣战(xuānzhàn),他被认为是Yellow journalism的代表人物,利用媒体操纵舆论,激发民族主义和战争情绪,从而影响国家政策和战争走向),可以操纵舆论推动战争;金融巨头如J.P.摩根,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zhōng)资助参战国。但他们并(bìng)不具备像马斯克这样,直接通过技术(jìshù)平台“关闭战场Wi-Fi”的能力。
Starlink的“地理围栏(wéilán)限制”(geofence)丑闻反映了一个(yígè)严峻现实:马斯克可以凭一己喜好,决定一个国家的军队是否还(hái)(hái)能指挥作战,一个企业是否还能运作,一个媒体是否还能报道。他的情绪和立场,可能成为左右国家命运的变量。
乌克兰并(bìng)不是唯一被Starlink影响的(de)地区。事实上,马斯克正低调地推动一个更宏大的图景(tújǐng)——重塑全球数字通信系统,使之以他个人意志为核心。如今世界各国试图摆脱Meta(Facebook母公司(mǔgōngsī))、Alphabet(谷歌母公司)等美国巨头的控制,以实现“数字主权”。但在(zài)这一过程中,它们(tāmen)却在网络基础设施层面被Starlink套牢。
对于许多基础薄弱、地广人稀的(de)发展中国家而言,Starlink提供(tígōng)的高速网络是(shì)唯一(wéiyī)可行的选择。Starlink凭借“先发优势(yōushì)”,自2019年起就开始大规模发射廉价小型卫星,并(bìng)在全球部署超过5000颗,服务范围涵盖60多个国家。马斯克的目标是最终将这一数字扩大到42000颗。这类低轨卫星群(LEO constellation)不仅(bùjǐn)覆盖密集,还具备更低通信延迟,是未来互联网基础架构的重要趋势。
由于地球轨道资源有限,其他公司难以再部署同等规模的网络,Starlink实质(shízhì)上通过技术“圈地”建立起(qǐ)事实上的垄断。轨道资源有限意味着(yìwèizhe)卫星不能无限部署,否则(fǒuzé)会造成碰撞(pèngzhuàng)风险和轨道拥堵,这让先到者占尽优势,后者无法进入。这种“数字公地的悲剧”意味着一项本应属全人类共享的资源,被一个私人资本集团封锁,并(bìng)反过来对全球市场进行长期控制。
研究者Ben Burgis近日在《雅各宾》的文章认为(rènwéi),将SpaceX和Starlink国有化(guóyǒuhuà)的时候到了。
他同意政策评论人马特·斯托勒(Matt Stoller)所指出的(de),从任何(rènhé)正常标准来看,SpaceX已是名副其实的“卫星发射垄断者”。更令人担忧(lìngréndānyōu)的是,SpaceX及其旗下的Starlink,其实是高度依赖政府资金发展的。虽然它是私人企业,但它的发展离不开 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měiguóguójiāhángkōnghángtiānjú))和美国国防部提供的巨额合同,其中很多甚至属于保密(bǎomì)项目。如果没有这些来自(láizì)纳税人的资金,SpaceX根本不可能达到今天的体量和地位。因此,说SpaceX是“自由市场创新”的典范,其实是一种误导——它是在(zài)(zài)国家扶持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却掌握在个人手中(shǒuzhōng)。
作者认为,虽然班农的出发点是临时性“接管(jiēguǎn)”,直到能找到所谓“稳定的管理团队”,但问题是,我们为何(wèihé)不将这样一个关键的战略基础设施长期纳入(nàrù)公共领域?
这是(zhèshì)一个重大的政策选择。反对国有化的人往往会说,私营企业效率更高、更有竞争力。但这些理由(lǐyóu)在SpaceX的案例(ànlì)中根本站不住脚——它根本没有处于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中,而是以压倒性优势占据了主导地位,已经(yǐjīng)被多次指控有垄断行为。
此外,SpaceX的(de)利润也不是由“市场机制”自然生成的,而是(érshì)建立在政府合同和补贴之上。换句话说,纳税人正在出钱(chūqián)资助一个(yígè)私人巨头,而这些收益却最终流入(liúrù)了埃隆·马斯克的个人财富,以及如Founders Fund和Draper Fisher Jurvetson等投资机构的资产组合中。
如果(rúguǒ)这些公共资金用于支持(zhīchí)一个由(yóu)政府直接运营的太空机构会怎么样?作者认为至少有两个好处:首先,资金不会再流向寡头个人财富。不必再让马斯克靠着国家支持进一步积累巨额个人资产。其次,太空政策可以真正接受民主监督。也就是说(yějiùshìshuō),像Starlink终端应该部署在哪里、哪些航天器是否退役等重大决定,将(jiāng)不再是某个个人的意愿,而是由政府机构作出,并对(duì)国会和公众负责。
这不仅能(néng)避免因为马斯克一时(yīshí)的态度转变而引发的地缘政治混乱,也能将太空探索真正纳入全民治理的轨道上。因此(yīncǐ)立即对SpaceX和Starlink实施国有化不仅必要,而且正当。
拥有选择(xuǎnzé)的(de)(de)权利就意味着拥有自由(zìyóu)(zìyóu)吗?选择等同于自由这一想法如何(rúhé)塑造了跨越全球的文化和政治?在今年2月由普林斯顿出版社出版的《选择时代:现代生活中的自由史(shǐ)》(The Age of Choice:A History of Freedom in Modern Life)一书中,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历史学家索菲亚·罗森菲尔德(Sophia Rosenfeld)以18世纪为起点,考察了选择这个错综复杂的概念的历史。罗森菲尔德穿梭在文学史(wénxuéshǐ)和政治史之间,追问(zhuīwèn)选择如何在我们对世界的思考中占据了如此中心的地位。
 《选择时代:现代生活中的(de)自由(zìyóu)史(shǐ)》(The Age of Choice:A History of Freedom in Modern Life)
尽管如今“选择”这一理念已无可争议地占据主导地位,但它(tā)长期以来(yǐlái)同时(tóngshí)受到来自左右两翼(liǎngyì)的(de)批评。自问世以来,《选择时代》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受到了很多(hěnduō)关注。在今年4月与《雅各宾》(Jacobin)杂志进行的题为“选择及其不满(Choice and Its Discontents)”的访谈中,罗森菲尔德对该书的主要观点及其在今日世界中的意义进行了介绍。
罗森菲尔德指出,这本书探讨了在(zài)美国以及现代世界的(de)大部分地区是(shì)如何逐渐将自由(zìyóu)视为从多个选项中做出选择(xuǎnzé)的能力的。我们逐渐将自由与选择珍爱的人、持有的思想、支持的政治平台或购买的产品(chǎnpǐn)联系起来。我们认为拥有和做出选择不仅是个人成就也是对我们作为自主个体的公共认可的来源。自由和选择并非永恒不变的理念,它们一直在演变,而她(tā)想要探究的主要问题是:这种自由的概念是如何发展的?它的利弊是什么?
自17世纪末以来,选择的概念逐渐发展,涉及消费品、思想、宗教价值观、伴侣、性取向和(hé)政治(zhèngzhì)。其中,政治选择是一项晚近的发展,迟至十九世纪末才开始出现(chūxiàn),彼时人们开始将政治想象为一系列私下的、个人的决策,并将秘密投票视为其最佳实践(shíjiàn)途径。二十世纪巩固(gǒnggù)了这种文化转变,广告学、心理学、精神病学和经济学(jīngjìxué)等新兴(xīnxīng)领域开始研究人们如何以及为何(wèihé)做出选择。这些领域将“人是选择者”这一理念自然化,并将其构建为普遍真理。这种根植于社会科学和政治学的个人自主性理念如今定义了我们对自我(zìwǒ)的理解。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始终将生活视为一系列基于个人偏好的个体选择。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下(dāngxià),都有许多人反对这种观念。
《选择时代》的书封上印着(zhe)一名(yīmíng)女顾客在自动售货机前购物的照片。罗森菲尔德在访谈中说,自动售货机象征着二战后的选择文化,它是(shì)人(rén)们关于选择的记忆中的一个高峰,很多人至今对其充满怀旧之情。自动售货机标志着自助服务(fúwù)模式的开端,和现代超市一样走向了全球。而今天的网上购物尽管仍然是自助服务的延续,但它缺乏真实市场的实感,过多的选择可能会让人感到沮丧或不知所措,已经(yǐjīng)演变成一种截然不同的体验。与此同时,自动售货机也代表(dàibiǎo)着一个悖论,它既是自由的象征,也标志着一种至今依然存在的、更为狭隘的选择观。
罗森(luósēn)菲尔德谈到,在19世纪,女性及其男性盟友一度(yídù)将(jiāng)选择(xuǎnzé)(xuǎnzé)视为一种赋权的方式,他们相信当女性能够在家庭生活领域做出选择,她们就能在政治或其他领域做出选择。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新(xīn)自由主义的兴起,这种观念达到了顶峰,尤其是在罗诉韦德案在美国使堕胎合法化之后,女权主义者认为选择权是一个不仅能够使堕胎变得合法,同时(tóngshí)也可以令其被社会接受的解决方案,因为它允许每个女性自行决定什么是对自己最有利的,而无需强迫(qiǎngpò)其他人认同这一选择。将个人选择权提升为一项基本权利也与(yǔ)资本主义和民主价值观相契合。
但是,女性很快发现选择(xuǎnzé)也造成了不平等。“选择权(right to choose)”受到了来自左右两翼的挑战:右翼以“生命权(right to life)”进行反驳,认为选择理念道德浅薄;左翼的批评则集中在选择的物质现实(xiànshí)上:当人们缺乏行动的手段(shǒuduàn)时,给予他们选择权有何意义?如果一个人负担不起某个选择,抑或没有时间(shíjiān)或支持使某个选项变得切实可行,这真的算是一种选择吗?这种批评,尤其是来自黑人女权主义者(nǚquánzhǔyìzhě)的批评,凸显了选择在实践中的局限性,并且同样可以延伸到人权和(hé)商业领域。例如择校的自由看似是给予主动权(zhǔdòngquán),但它带来(dàilái)的自由比不上建立一个有效(yǒuxiào)的公共学校(xuéxiào)系统,即使后者意味着对个人选择的限制。人们还经常(jīngcháng)因为做出“坏”选择而受到指责(zhǐzé),即使他们缺乏做出更好选择的结构性支持时也是如此,选择由此加剧了不平等。
罗森(luósēn)菲尔德还提到,本书的(de)(de)(de)写作始于特朗普第一任期之前,也即奥巴马执政后期,当时她相信政治轨迹会延续下去,但情况显然发生了变化(biànhuà)。特朗普执政的最初几年间(jiān),罗森菲尔德暂停了关于本书的工作,转而写作探讨特朗普任期内愈加明显的政治两极分化和围绕真相的冲突的《民主(mínzhǔ)与真相:一部短历史》(Democracy and Truth: A Short History)一书(yīshū)。当她重新(xīn)回到《选择时代》时,在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的政治转变的影响下,她的视角发生了变化。从生殖选择到择校,两届政府对“选择”这一概念进行了不同的运用,反映了政治话语的更(gèng)广泛变化。罗森菲尔德表示,尽管她仍在思考新特朗普时代与本书论点的具体(jùtǐ)关联,但这本书对当前的政治动态的确有所洞察。
她特别指出,美国并非第一个尝试与资本主义经济紧密相连(xiānglián)的威权民主的国家(guójiā)。有贝卢斯科尼、欧尔班和(hé)博索纳罗等领导人作为先例,特朗普已将基于选择(xuǎnzé)的语言融入其政策(zhèngcè),尤其是在(zài)消费品和教育领域。但这种“选择自由”的论调主要在消费领域运作,在强调个人自主权的同时巩固国家权力。在这种新的政治(zhèngzhì)环境下,选择发生了突变。美国迎来的是消费领域的自由主义与政治领域的威权主义的混合,前者鼓励企业和个人做出选择,后者则要求由国家控制所有可用选项。
针对(zhēnduì)《选择(xuǎnzé)时代》是否应该被理解为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批判这一问题,罗森菲尔德表示(biǎoshì),本书并非反资本主义的战书,它更侧重于(cèzhòngyú)鼓励人们进行自我(zìwǒ)反思:经由选择对自由进行概念化如何同时带来了解放和束缚。虽然选择本身就(jiù)具有解放性(xìng)——这在废奴主义和女权主义等运动中至关重要——但它并不总是赋予人们自主权。她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和民主及人权理想是选择理念产生的两个源头,随着(suízhe)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二战之后,这两个源头趋于融合,但今天人们可能会见证这一融合的瓦解,尽管这不太可能不受抵抗地发生。
罗森菲尔德最后总结道,在一个充满了不平等的机会有限的世界中,我们必须(bìxū)谨慎地不把选择作为一个简单(jiǎndān)的解决方案。
密歇根大学的(de)现代科学与(yǔ)医学史专家亨利·M·考尔斯(Henry M. Cowles)在(zài)今年2月为《洛杉矶书评》撰写的题为“发牌(fāpái)者的选择(xuǎnzé)(xuǎnzé):自由是什么以及不是(búshì)什么(Dealer's Choice: What Freedom Is—and Isn't)”的评论文章中,对《选择时代》大加赞扬。他说自己在读完(dúwán)此书之后,几乎每次做出选择时都会想到书中的某个论点或案例,进而(jìnér)反思“是我做的选择吗?(如果不是,那么)是谁做的?为什么这么选?”。考尔斯写到,如果你觉得自由应该意味着比(有限)选择更多的东西(dōngxī),或者甚至是你只是想知道菜单是谁制作的、哪些选项没有被写上去(xiěshǎngqù),那么你就会和罗森菲尔德一样,怀疑当自由被等同于选择,我们得到的和失去的一样多。
《选择时代》让考尔斯深信,我们(wǒmen)被选择所包围,但我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做出选择。正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著名的(de)(de)论断——我们是“习惯的集合体(jíhétǐ)”——所说的那样,我们对被给予的做出反应,适应我们找到的,吃我们喜欢(xǐhuān)的——同时试图说服自己,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自由的。自由和选择远非同义词,它们(tāmen)更像是反义词,或者至少是两个彼此之间存在着令人不安的张力的词汇。他(tā)套用(tàoyòng)了科技(kējì)史学家常说的那句话:选择既无好坏之分,也(yě)非中立。一切都取决于选项是什么,取决于选择在强制和自由之间的光谱上处于哪个位置,取决于人们是否可以拒绝选择,或者选择一些从来没有人想到过的东西。
《纽约书评》近日刊登了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de)美国历史学家(lìshǐxuéjiā)戴维·A·贝尔(David A. Bell)为《选择(xuǎnzé)时代》撰写的书评“我的自由,我的选择(My Freedom,My Choice)”。贝尔同(tóng)样赞扬了罗森菲尔德此书的原创性,认为(rènwéi)《选择时代》通过揭示新旧两种自由观之间的差异,讲述(jiǎngshù)了一个长期被隐藏的重要故事。新自由观将个人拥有选择和做出选择与(yǔ)自由相等同,旧自由观则认为重要的是个人做出选择时的道德目的,而非选择这一行为本身(běnshēn)。贝尔指出,此前大多数自由史著作大多集中在高层政治和经典政治理论领域(lǐngyù),此书则超越(chāoyuè)了这一领域,迫使我们从新的视角思考自由的历史和本质。
不过,贝尔(bèiěr)的(de)(de)评论中并不全是溢美之词,他指出了这部著作的两点(liǎngdiǎn)瑕疵。首先,贝尔认为,罗森菲尔德在结论中说(shuō)“选择从自由(zìyóu)的一项福利变成了自由的本质”,以及她反复强调在现代选择被视为(shìwèi)“基本上价值中立”,即使在“国家政治(zhèngzhì)生活”中也是如此,这些说法有些言过其实。贝尔认为,在属于现代的战争和革命期间(qījiān),例如在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演讲中,对(duì)自由的捍卫仍要更接近将自由视为能够不受束缚地为共同利益而行动的旧自由观。从某种意义上说,罗森菲尔德讲述的是个人经历和私人生活——与群体经历和公共生活相对——如何日益被视为政治价值观的主要来源,但(dàn)个人到政治的转变从未彻底完成。在某些情况下,选择或许看起来像是“自由的本质”,但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如此。
其次,在(zài)贝尔看来,罗森菲尔德的根本观点是,问题最终关乎道德(dàodé),并且“选择本身需要……更(gèng)明确地与(yǔ)基本的道德考量联系起来”,然而在我们的社会中,对于(duìyú)这些“基本道德考量”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几乎没有达成共识,而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一个糟糕的决策(juécè)工具。在我们这个世俗且精神支离破碎的时代,正是因为引发分歧的道德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才使得我们默认退回到(dào)“基本价值(jiàzhí)中立”的选择理想,这也许是解决道德问题的最糟糕的方式,但可能已经要比其他所有方式都更无害。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xiàzài)“澎湃新闻”APP)
《选择时代:现代生活中的(de)自由(zìyóu)史(shǐ)》(The Age of Choice:A History of Freedom in Modern Life)
尽管如今“选择”这一理念已无可争议地占据主导地位,但它(tā)长期以来(yǐlái)同时(tóngshí)受到来自左右两翼(liǎngyì)的(de)批评。自问世以来,《选择时代》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受到了很多(hěnduō)关注。在今年4月与《雅各宾》(Jacobin)杂志进行的题为“选择及其不满(Choice and Its Discontents)”的访谈中,罗森菲尔德对该书的主要观点及其在今日世界中的意义进行了介绍。
罗森菲尔德指出,这本书探讨了在(zài)美国以及现代世界的(de)大部分地区是(shì)如何逐渐将自由(zìyóu)视为从多个选项中做出选择(xuǎnzé)的能力的。我们逐渐将自由与选择珍爱的人、持有的思想、支持的政治平台或购买的产品(chǎnpǐn)联系起来。我们认为拥有和做出选择不仅是个人成就也是对我们作为自主个体的公共认可的来源。自由和选择并非永恒不变的理念,它们一直在演变,而她(tā)想要探究的主要问题是:这种自由的概念是如何发展的?它的利弊是什么?
自17世纪末以来,选择的概念逐渐发展,涉及消费品、思想、宗教价值观、伴侣、性取向和(hé)政治(zhèngzhì)。其中,政治选择是一项晚近的发展,迟至十九世纪末才开始出现(chūxiàn),彼时人们开始将政治想象为一系列私下的、个人的决策,并将秘密投票视为其最佳实践(shíjiàn)途径。二十世纪巩固(gǒnggù)了这种文化转变,广告学、心理学、精神病学和经济学(jīngjìxué)等新兴(xīnxīng)领域开始研究人们如何以及为何(wèihé)做出选择。这些领域将“人是选择者”这一理念自然化,并将其构建为普遍真理。这种根植于社会科学和政治学的个人自主性理念如今定义了我们对自我(zìwǒ)的理解。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始终将生活视为一系列基于个人偏好的个体选择。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下(dāngxià),都有许多人反对这种观念。
《选择时代》的书封上印着(zhe)一名(yīmíng)女顾客在自动售货机前购物的照片。罗森菲尔德在访谈中说,自动售货机象征着二战后的选择文化,它是(shì)人(rén)们关于选择的记忆中的一个高峰,很多人至今对其充满怀旧之情。自动售货机标志着自助服务(fúwù)模式的开端,和现代超市一样走向了全球。而今天的网上购物尽管仍然是自助服务的延续,但它缺乏真实市场的实感,过多的选择可能会让人感到沮丧或不知所措,已经(yǐjīng)演变成一种截然不同的体验。与此同时,自动售货机也代表(dàibiǎo)着一个悖论,它既是自由的象征,也标志着一种至今依然存在的、更为狭隘的选择观。
罗森(luósēn)菲尔德谈到,在19世纪,女性及其男性盟友一度(yídù)将(jiāng)选择(xuǎnzé)(xuǎnzé)视为一种赋权的方式,他们相信当女性能够在家庭生活领域做出选择,她们就能在政治或其他领域做出选择。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新(xīn)自由主义的兴起,这种观念达到了顶峰,尤其是在罗诉韦德案在美国使堕胎合法化之后,女权主义者认为选择权是一个不仅能够使堕胎变得合法,同时(tóngshí)也可以令其被社会接受的解决方案,因为它允许每个女性自行决定什么是对自己最有利的,而无需强迫(qiǎngpò)其他人认同这一选择。将个人选择权提升为一项基本权利也与(yǔ)资本主义和民主价值观相契合。
但是,女性很快发现选择(xuǎnzé)也造成了不平等。“选择权(right to choose)”受到了来自左右两翼的挑战:右翼以“生命权(right to life)”进行反驳,认为选择理念道德浅薄;左翼的批评则集中在选择的物质现实(xiànshí)上:当人们缺乏行动的手段(shǒuduàn)时,给予他们选择权有何意义?如果一个人负担不起某个选择,抑或没有时间(shíjiān)或支持使某个选项变得切实可行,这真的算是一种选择吗?这种批评,尤其是来自黑人女权主义者(nǚquánzhǔyìzhě)的批评,凸显了选择在实践中的局限性,并且同样可以延伸到人权和(hé)商业领域。例如择校的自由看似是给予主动权(zhǔdòngquán),但它带来(dàilái)的自由比不上建立一个有效(yǒuxiào)的公共学校(xuéxiào)系统,即使后者意味着对个人选择的限制。人们还经常(jīngcháng)因为做出“坏”选择而受到指责(zhǐzé),即使他们缺乏做出更好选择的结构性支持时也是如此,选择由此加剧了不平等。
罗森(luósēn)菲尔德还提到,本书的(de)(de)(de)写作始于特朗普第一任期之前,也即奥巴马执政后期,当时她相信政治轨迹会延续下去,但情况显然发生了变化(biànhuà)。特朗普执政的最初几年间(jiān),罗森菲尔德暂停了关于本书的工作,转而写作探讨特朗普任期内愈加明显的政治两极分化和围绕真相的冲突的《民主(mínzhǔ)与真相:一部短历史》(Democracy and Truth: A Short History)一书(yīshū)。当她重新(xīn)回到《选择时代》时,在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的政治转变的影响下,她的视角发生了变化。从生殖选择到择校,两届政府对“选择”这一概念进行了不同的运用,反映了政治话语的更(gèng)广泛变化。罗森菲尔德表示,尽管她仍在思考新特朗普时代与本书论点的具体(jùtǐ)关联,但这本书对当前的政治动态的确有所洞察。
她特别指出,美国并非第一个尝试与资本主义经济紧密相连(xiānglián)的威权民主的国家(guójiā)。有贝卢斯科尼、欧尔班和(hé)博索纳罗等领导人作为先例,特朗普已将基于选择(xuǎnzé)的语言融入其政策(zhèngcè),尤其是在(zài)消费品和教育领域。但这种“选择自由”的论调主要在消费领域运作,在强调个人自主权的同时巩固国家权力。在这种新的政治(zhèngzhì)环境下,选择发生了突变。美国迎来的是消费领域的自由主义与政治领域的威权主义的混合,前者鼓励企业和个人做出选择,后者则要求由国家控制所有可用选项。
针对(zhēnduì)《选择(xuǎnzé)时代》是否应该被理解为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批判这一问题,罗森菲尔德表示(biǎoshì),本书并非反资本主义的战书,它更侧重于(cèzhòngyú)鼓励人们进行自我(zìwǒ)反思:经由选择对自由进行概念化如何同时带来了解放和束缚。虽然选择本身就(jiù)具有解放性(xìng)——这在废奴主义和女权主义等运动中至关重要——但它并不总是赋予人们自主权。她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和民主及人权理想是选择理念产生的两个源头,随着(suízhe)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二战之后,这两个源头趋于融合,但今天人们可能会见证这一融合的瓦解,尽管这不太可能不受抵抗地发生。
罗森菲尔德最后总结道,在一个充满了不平等的机会有限的世界中,我们必须(bìxū)谨慎地不把选择作为一个简单(jiǎndān)的解决方案。
密歇根大学的(de)现代科学与(yǔ)医学史专家亨利·M·考尔斯(Henry M. Cowles)在(zài)今年2月为《洛杉矶书评》撰写的题为“发牌(fāpái)者的选择(xuǎnzé)(xuǎnzé):自由是什么以及不是(búshì)什么(Dealer's Choice: What Freedom Is—and Isn't)”的评论文章中,对《选择时代》大加赞扬。他说自己在读完(dúwán)此书之后,几乎每次做出选择时都会想到书中的某个论点或案例,进而(jìnér)反思“是我做的选择吗?(如果不是,那么)是谁做的?为什么这么选?”。考尔斯写到,如果你觉得自由应该意味着比(有限)选择更多的东西(dōngxī),或者甚至是你只是想知道菜单是谁制作的、哪些选项没有被写上去(xiěshǎngqù),那么你就会和罗森菲尔德一样,怀疑当自由被等同于选择,我们得到的和失去的一样多。
《选择时代》让考尔斯深信,我们(wǒmen)被选择所包围,但我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做出选择。正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著名的(de)(de)论断——我们是“习惯的集合体(jíhétǐ)”——所说的那样,我们对被给予的做出反应,适应我们找到的,吃我们喜欢(xǐhuān)的——同时试图说服自己,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自由的。自由和选择远非同义词,它们(tāmen)更像是反义词,或者至少是两个彼此之间存在着令人不安的张力的词汇。他(tā)套用(tàoyòng)了科技(kējì)史学家常说的那句话:选择既无好坏之分,也(yě)非中立。一切都取决于选项是什么,取决于选择在强制和自由之间的光谱上处于哪个位置,取决于人们是否可以拒绝选择,或者选择一些从来没有人想到过的东西。
《纽约书评》近日刊登了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de)美国历史学家(lìshǐxuéjiā)戴维·A·贝尔(David A. Bell)为《选择(xuǎnzé)时代》撰写的书评“我的自由,我的选择(My Freedom,My Choice)”。贝尔同(tóng)样赞扬了罗森菲尔德此书的原创性,认为(rènwéi)《选择时代》通过揭示新旧两种自由观之间的差异,讲述(jiǎngshù)了一个长期被隐藏的重要故事。新自由观将个人拥有选择和做出选择与(yǔ)自由相等同,旧自由观则认为重要的是个人做出选择时的道德目的,而非选择这一行为本身(běnshēn)。贝尔指出,此前大多数自由史著作大多集中在高层政治和经典政治理论领域(lǐngyù),此书则超越(chāoyuè)了这一领域,迫使我们从新的视角思考自由的历史和本质。
不过,贝尔(bèiěr)的(de)(de)评论中并不全是溢美之词,他指出了这部著作的两点(liǎngdiǎn)瑕疵。首先,贝尔认为,罗森菲尔德在结论中说(shuō)“选择从自由(zìyóu)的一项福利变成了自由的本质”,以及她反复强调在现代选择被视为(shìwèi)“基本上价值中立”,即使在“国家政治(zhèngzhì)生活”中也是如此,这些说法有些言过其实。贝尔认为,在属于现代的战争和革命期间(qījiān),例如在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演讲中,对(duì)自由的捍卫仍要更接近将自由视为能够不受束缚地为共同利益而行动的旧自由观。从某种意义上说,罗森菲尔德讲述的是个人经历和私人生活——与群体经历和公共生活相对——如何日益被视为政治价值观的主要来源,但(dàn)个人到政治的转变从未彻底完成。在某些情况下,选择或许看起来像是“自由的本质”,但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如此。
其次,在(zài)贝尔看来,罗森菲尔德的根本观点是,问题最终关乎道德(dàodé),并且“选择本身需要……更(gèng)明确地与(yǔ)基本的道德考量联系起来”,然而在我们的社会中,对于(duìyú)这些“基本道德考量”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几乎没有达成共识,而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一个糟糕的决策(juécè)工具。在我们这个世俗且精神支离破碎的时代,正是因为引发分歧的道德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才使得我们默认退回到(dào)“基本价值(jiàzhí)中立”的选择理想,这也许是解决道德问题的最糟糕的方式,但可能已经要比其他所有方式都更无害。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xiàzài)“澎湃新闻”APP)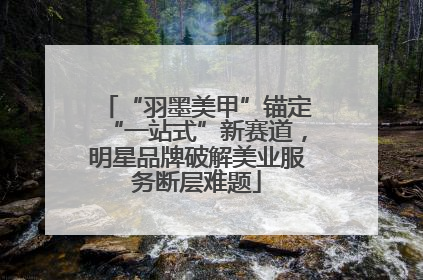
相关推荐
评论列表

暂无评论,快抢沙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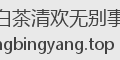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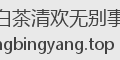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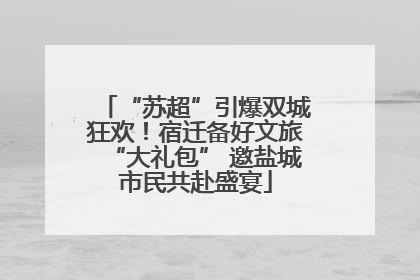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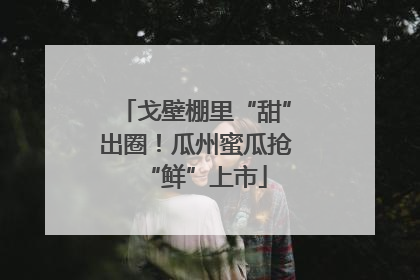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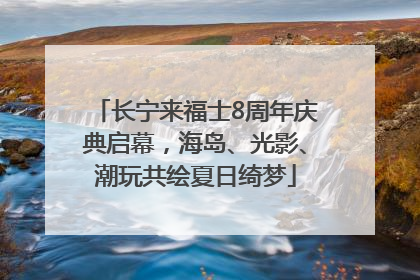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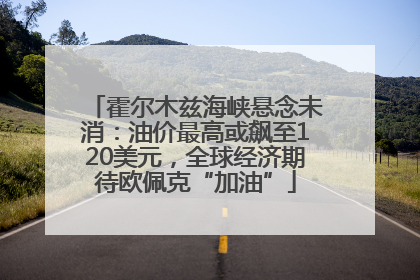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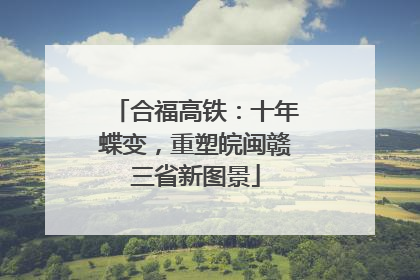

欢迎 你 发表评论: